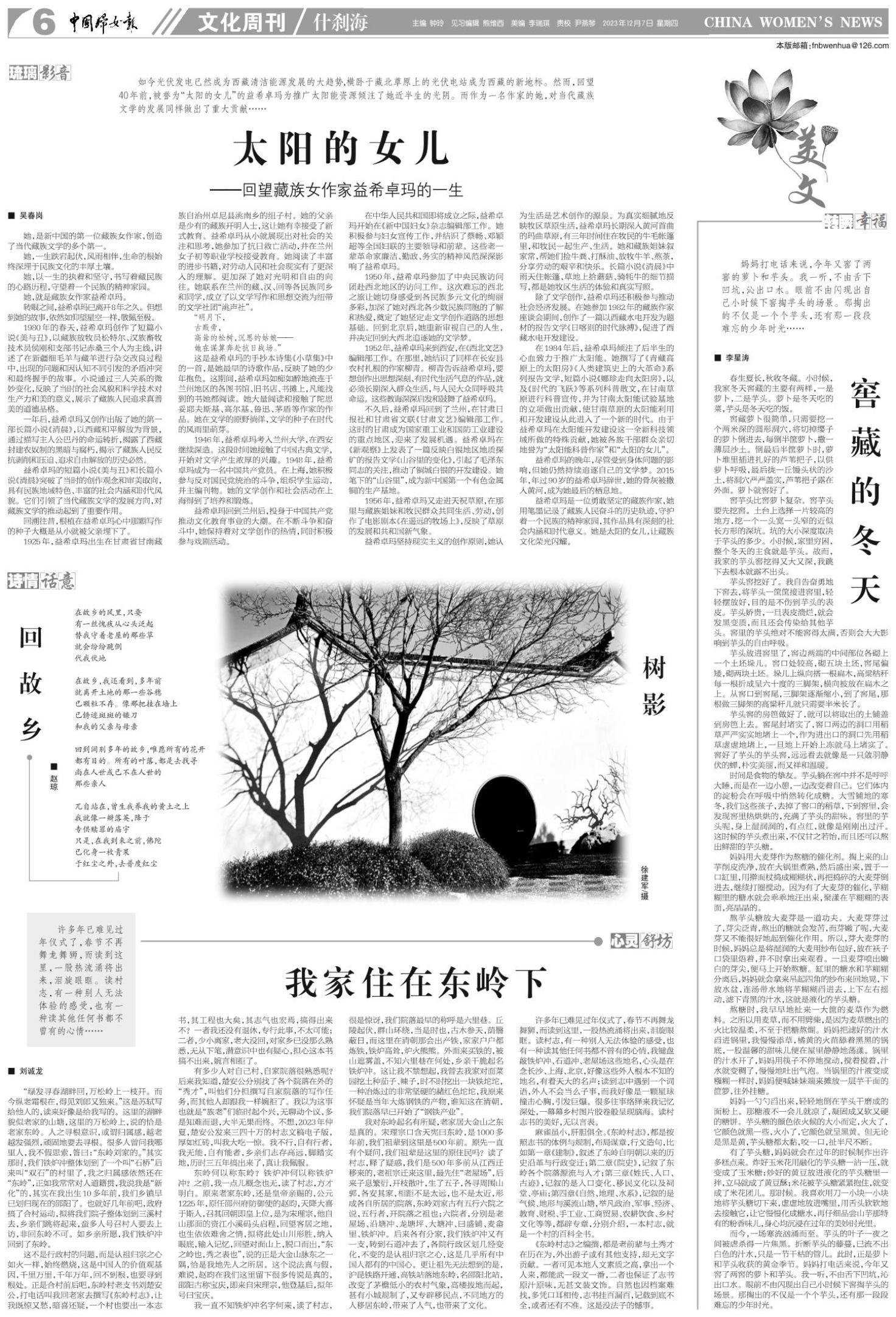■ 吴春岗
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位藏族女作家,创造了当代藏族文学的多个第一。
她,一生跌宕起伏,风雨相伴,生命的根始终深埋于民族文化的丰厚土壤。
她,以一生的执着和坚守,书写着藏民族的心路历程,守望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她,就是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
转眼之间,益希卓玛已离开8年之久。但想到她的故事,依然如仰望星空一样,敬佩至极。
1980年的春天,益希卓玛创作了短篇小说《美与丑》,以藏族放牧员松特尔、汉族畜牧技术员侯刚和支部书记赤桑三个人为主线,讲述了在新疆细毛羊与藏羊进行杂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因认知不同引发的矛盾冲突和最终握手的故事。小说通过三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美的意义,展示了藏族人民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品格。
一年后,益希卓玛又创作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晨》,以西藏和平解放为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巴丹的命运转折,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与腐朽,揭示了藏族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必然。
益希卓玛的短篇小说《美与丑》和长篇小说《清晨》突破了当时的创作观念和审美取向,具有民族地域特色、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时代风貌。它们引领了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方向,对藏族文学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溯往昔,根植在益希卓玛心中那颗写作的种子大概是从小就被父亲埋下了。
1925年,益希卓玛出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南乡的纽子村。她的父亲是少有的藏族开明人士,这让她有幸接受了新式教育。益希卓玛从小就展现出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她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兰州女子初等职业学校接受教育。她阅读了丰富的进步书籍,对劳动人民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更加深了她对光明和自由的向往。她联系在兰州的藏、汉、回等各民族同乡和同学,成立了以文学写作和思想交流为纽带的文学社团“洮声社”。
“明月下,
古殿旁,
高耸的松树,沉思的姑娘——
她在谋算奔赴抗日战场。”
这是益希卓玛的手抄本诗集《小草集》中的一首,是她最早的诗歌作品,反映了她的少年抱负。这期间,益希卓玛如痴如醉地流连于兰州地区的各图书馆、旧书店、书摊上,凡能找到的书她都阅读。她大量阅读和接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她在文学的原野徜徉,文学的种子在时代的风雨里萌芽。
1946年,益希卓玛考入兰州大学,在西安继续深造。这段时间她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48年,益希卓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在上海,她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组织学生运动,并主编刊物。她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在上海得到了培养和锻炼。
益希卓玛回到兰州后,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大潮。在不断斗争和奋斗中,她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同时积极参与戏剧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益希卓玛开始在《新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工作。她积极参与妇女宣传工作,并结识了蔡畅、邓颖超等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和前辈。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廉洁、勤政、务实的精神风范深深影响了益希卓玛。
1950年,益希卓玛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北地区的访问工作。这次难忘的西北之旅让她切身感受到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绚丽多彩,加深了她对西北各少数民族同胞的了解和热爱,奠定了她坚定走文学创作道路的思想基础。回到北京后,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决定回到大西北追逐她的文学梦。
1952年,益希卓玛来到西安,在《西北文艺》编辑部工作。在那里,她结识了同样在长安县农村扎根的作家柳青。柳青告诉益希卓玛,要想创作出思想深刻、有时代生活气息的作品,就必须长期深入群众生活,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些教诲深深启发和鼓舞了益希卓玛。
不久后,益希卓玛回到了兰州,在甘肃日报社和甘肃省文联《甘肃文艺》编辑部工作。这时的甘肃成为国家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迎来了发展机遇。益希卓玛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反映白银地区地质探矿的报告文学《山谷里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推动了铜城白银的开发建设。她笔下的“山谷里”,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色金属铜的生产基地。
1956年,益希卓玛又走进天祝草原,在那里与藏族姐妹和牧民群众共同生活、劳动,创作了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反映了草原的发展和共和国新气象。
益希卓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她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为真实细腻地反映牧区草原生活,益希卓玛长期深入黄河首曲的玛曲草原,有三年时间住在牧民的牛毛帐篷里,和牧民一起生产、生活。她和藏族姐妹叙家常,帮她们捡牛粪、打酥油、放牧牛羊、熬茶,分享劳动的艰辛和快乐。长篇小说《清晨》中雨天住帐篷、草地上拾蘑菇、骑牦牛的细节描写,都是她牧区生活的体验和真实写照。
除了文学创作,益希卓玛还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她参加1982年的藏族作家座谈会期间,创作了一篇以西藏水电开发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日喀则的时代脉搏》,促进了西藏水电开发建设。
在1984年后,益希卓玛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推广太阳能。她撰写了《青藏高原上的太阳房》《人类建筑史上的大革命》系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娜珍走向太阳房》,以及《时代的飞跃》等系列科普散文,在甘南草原进行科普宣传,并为甘南太阳能试验基地的立项做出贡献,使甘南草原的太阳能利用和开发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益希卓玛在太阳能开发建设这一全新科技领域所做的特殊贡献,她被各族干部群众亲切地誉为“太阳能科普作家”和“太阳的女儿”。
益希卓玛的晚年,尽管受到身体问题的影响,但她仍然持续追逐自己的文学梦。2015年,年过90岁的益希卓玛辞世,她的骨灰被撒入黄河,成为她最后的栖息地。
益希卓玛是一位勇敢坚定的藏族作家,她用笔墨记录了藏族人民奋斗的历史轨迹,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其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时代意义。她是太阳的女儿,让藏族文化荣光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