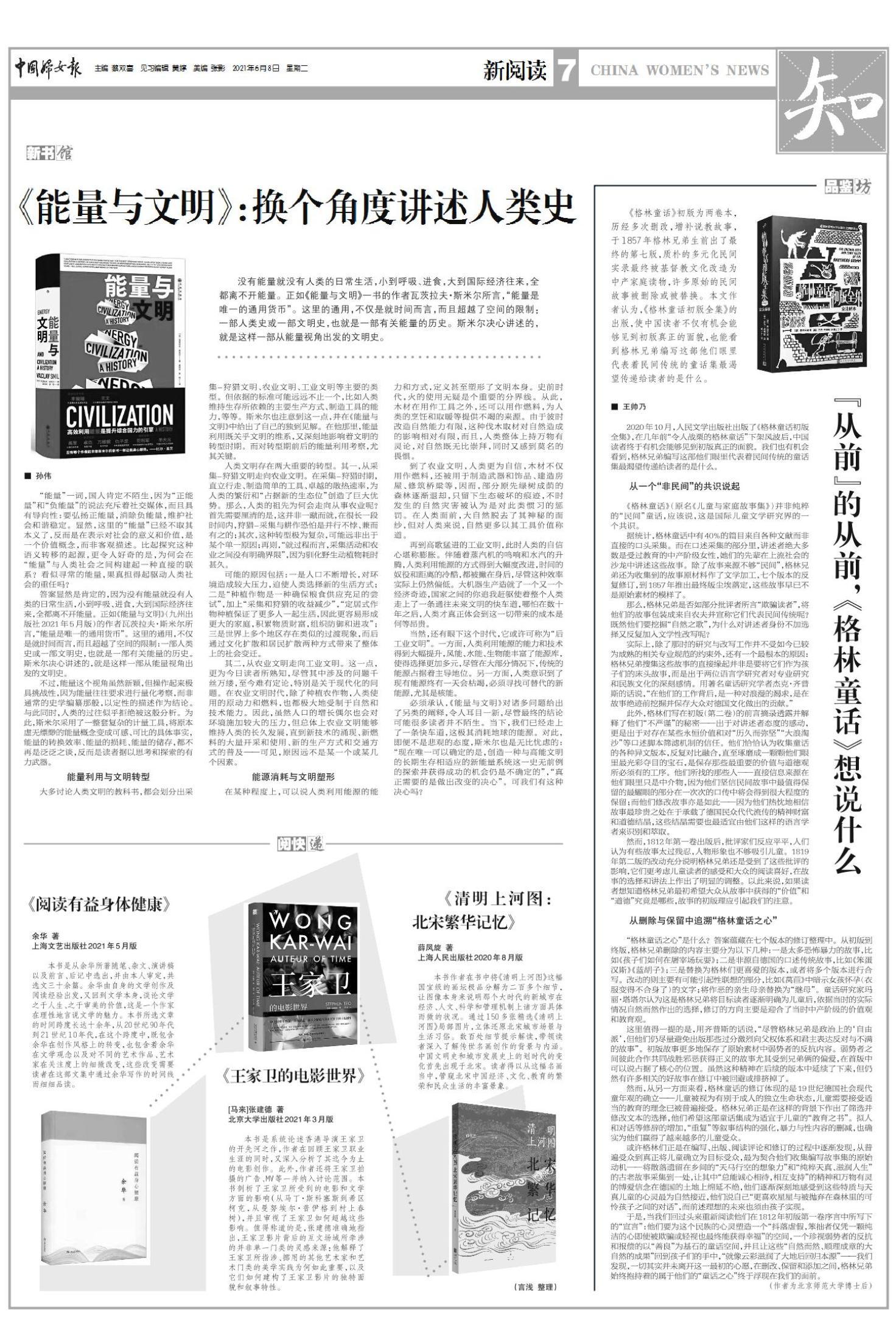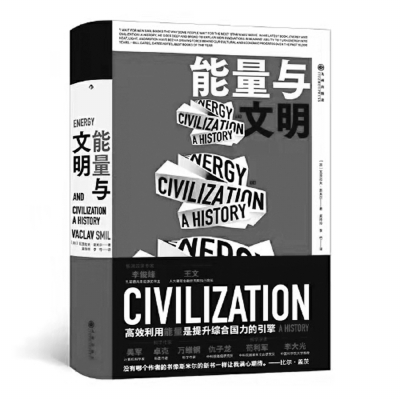没有能量就没有人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来,全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一书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言,“能量是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一部人类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斯米尔决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发的文明史。
■ 孙伟
“能量”一词,国人肯定不陌生,因为“正能量”和“负能量”的说法充斥着社交媒体,而且具有导向性:要弘扬正能量,消除负能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显然,这里的“能量”已经不取其本义了,反而是在表示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客观描述。比起探究这种语义转移的起源,更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会在“能量”与人类社会之间构建起一种直接的联系?看似寻常的能量,果真担得起驱动人类社会的重任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能量就没有人类的日常生活,小到呼吸、进食,大到国际经济往来,全都离不开能量。正如《能量与文明》(九州出版社2021年5月版)的作者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言,“能量是唯一的通用货币”。这里的通用,不仅是就时间而言,而且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一部人类史或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有关能量的历史。斯米尔决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部从能量视角出发的文明史。
不过,能量这个视角虽然新颖,但操作起来极具挑战性,因为能量往往要求进行量化考察,而非通常的史学编纂那般,以定性的描述作为结论。与此同时,人类的过往似乎拒绝被这般分析。为此,斯米尔采用了一整套复杂的计量工具,将原本虚无缥缈的能量概念变成可感、可比的具体事实,能量的转换效率、能量的损耗、能量的储存,都不再是泛泛之谈,反而是读者据以思考和探索的有力武器。
能量利用与文明转型
大多讨论人类文明的教科书,都会划分出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主要的类型。但依据的标准可能远远不止一个,比如人类维持生存所依赖的主要生产方式、制造工具的能力,等等。斯米尔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在《能量与文明》中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那里,能量利用既关乎文明的维系,又深刻地影响着文明的转型时期。而对转型期前后的能量利用考察,尤其关键。
人类文明存在两大重要的转型。其一,从采集-狩猎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在采集-狩猎时期,直立行走、制造简单的工具、卓越的散热速率,为人类的繁衍和“占据新的生态位”创造了巨大优势。那么,人类的祖先为何会走向从事农业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并非一蹴而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狩猎-采集与耕作恐怕是并行不悖、兼而有之的;其次,这种转型极为复杂,可能远非出于某个单一原因;再则,“就过程而言,采集活动和农业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因为驯化野生动植物耗时甚久。
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人口不断增长,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迫使人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二是“种植作物是一种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的尝试”,加上“采集和狩猎的收益减少”,“定居式作物种植保证了更多人一起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更大的家庭,积累物质财富,组织防御和进攻”;三是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类似的过渡现象,而后通过文化扩散和居民扩散两种方式带来了整体上的社会变迁。
其二,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一点,更为今日读者所熟知,尽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千丝万缕,至今难有定论,特别是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在农业文明时代,除了种植农作物,人类使用的原动力和燃料,也都极大地受制于自然和技术能力。因此,虽然人口的增长偶尔也会对环境施加较大的压力,但总体上农业文明能够维持人类的长久发展,直到新技术的涌现、新燃料的大量开采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通方式的普及——可见,原因远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
能源消耗与文明塑形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和方式,定义甚至塑形了文明本身。史前时代,火的使用无疑是个重要的分界线。从此,木材在用作工具之外,还可以用作燃料,为人类的烹饪和取暖等提供不竭的来源。由于彼时改造自然能力有限,这种伐木取材对自然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人类整体上持万物有灵论,对自然既无比崇拜,同时又感到莫名的畏惧。
到了农业文明,人类更为自信,木材不仅用作燃料,还被用于制造武器和饰品、建造房屋、修筑桥梁等,因而,部分原先绿树成荫的森林逐渐退却,只留下生态破坏的痕迹,不时发生的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对此类惯习的惩罚。在人类面前,大自然脱去了其神秘的面纱,但对人类来说,自然更多以其工具价值称道。
再到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的自信心堪称膨胀。伴随着蒸汽机的鸣响和水汽的升腾,人类利用能源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改进,时间的奴役和距离的冷酷,都被撇在身后,尽管这种效率实际上仍然偏低。大机器生产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国家之间的你追我赶驱使着整个人类走上了一条通往未来文明的快车道,哪怕在数十年之后,人类才真正体会到这一切带来的成本是何等昂贵。
当然,还有眼下这个时代,它或许可称为“后工业文明”。一方面,人类利用能源的能力和技术得到大幅提升,风能、水能、生物能丰富了能源库,使得选择更加多元,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传统的能源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人类意识到了现有能源终有一天会枯竭,必须寻找可替代的新能源,尤其是核能。
必须承认,《能量与文明》对诸多问题给出了另类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最终的结论可能很多读者并不陌生。当下,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快车道,这极其消耗地球的能源。对此,即便不是悲观的态度,斯米尔也是无比忧虑的:“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创造一种与高能文明的长期生存相适应的新能量系统这一史无前例的探索并获得成功的机会仍是不确定的”,“真正需要的是做出改变的决心”。可我们有这种决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