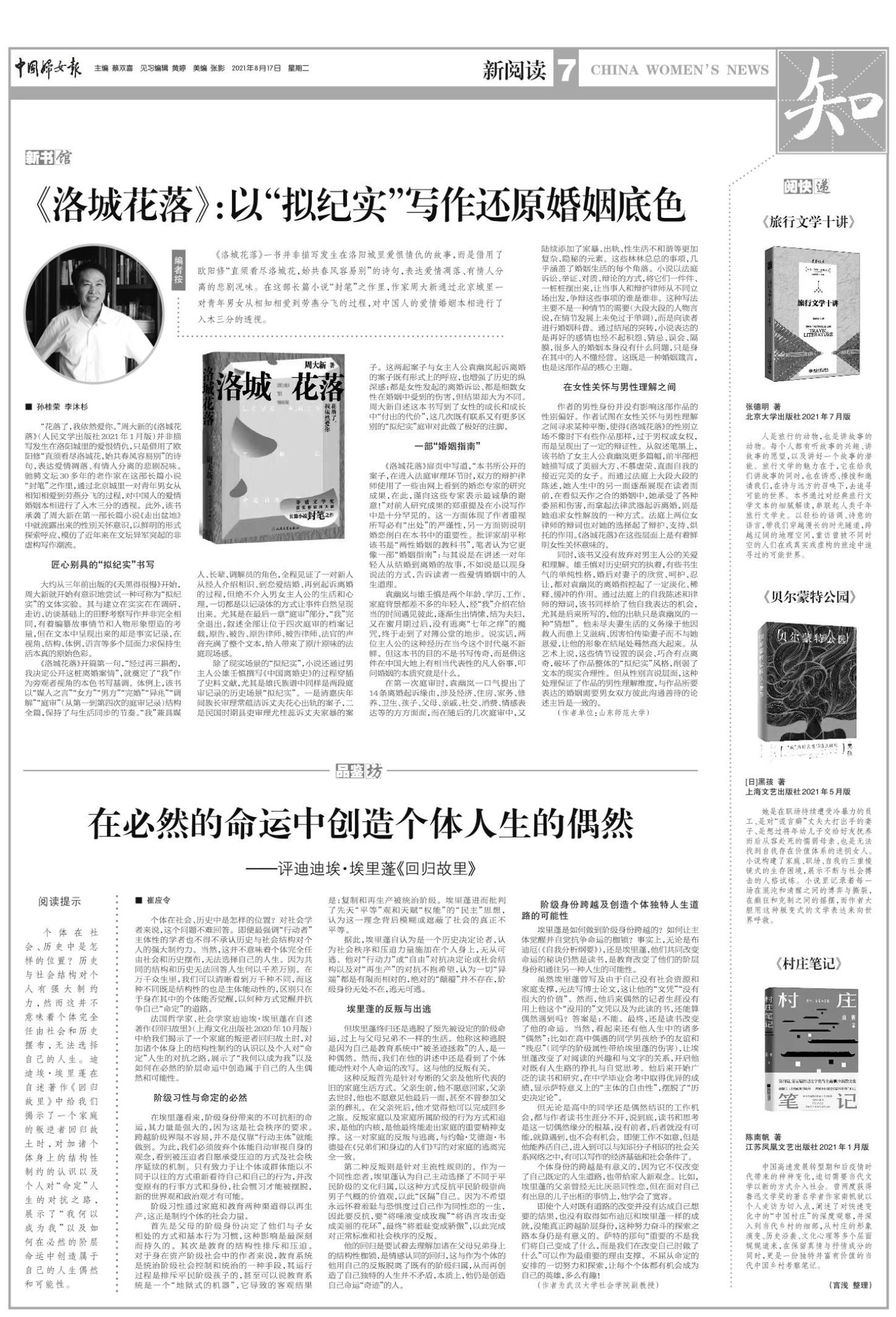阅读提示
个体在社会、历史中是怎样的位置?历史与社会结构对个人有强大制约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任由社会和历史摆布,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迪迪埃·埃里蓬在自述著作《回归故里》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家庭的叛逆者回归故土时,对加诸个体身上的结构性制约的认识以及个人对“命定”人生的对抗之路,展示了“我何以成为我”以及如何在必然的阶层命运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偶然和可能性。
■ 崔应令
个体在社会、历史中是怎样的位置?对社会学者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即便最强调“行动者”主体性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与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强大制约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任由社会和历史摆布,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因为共同的结构和历史无法回答人生何以千差万别。在万千众生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万千种不同,而这种不同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主体能动性的,区别只在于身在其中的个体能否觉醒,以何种方式觉醒并抗争自己“命定”的道路。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自述著作《回归故里》(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家庭的叛逆者回归故土时,对加诸个体身上的结构性制约的认识以及个人对“命定”人生的对抗之路,展示了“我何以成为我”以及如何在必然的阶层命运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偶然和可能性。
阶级习性与命定的必然
在埃里蓬看来,阶级身份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其力量是强大的,因为这是社会秩序的要求。跨越阶级界限不容易,并不是仅靠“行动主体”就能做到。为此,我们必须放弃个体能自动审视自身的观念,看到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及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只有致力于让个体或群体能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并改变原有的行事方式和身份,社会惯习才能被摆脱,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才有可能。
阶级习性通过家庭和教育两种渠道得以再生产,这正是制约个体的社会力量。
首先是父母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方式和基本行为习惯,这种影响是最深刻而持久的。其次是教育的结构性排斥和压迫。对于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者来说,教育系统是统治阶级社会控制和统治的一种手段,其运行过程是排斥平民阶级孩子的,甚至可以说教育系统是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它导致的客观结果是:复制和再生产被统治阶级。埃里蓬进而批判了先天“平等”观和天赋“权能”的“民主”思想,认为这一理念背后模糊或遮蔽了社会的真正不平等。
据此,埃里蓬自认为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社会秩序和压迫力量施加在个人身上,无从可逃。他对“行动力”或“自由”对抗决定论或社会结构以及对“再生产”的对抗不抱希望,认为一切“异端”都是有限而相对的,绝对的“颠覆”并不存在,阶级身份无处不在,逃无可逃。
埃里蓬的反叛与出逃
但埃里蓬终归还是逃脱了预先被设定的阶级命运,过上与父母兄弟不一样的生活。他称这种逃脱是因为自己是教育系统中“被圣迹拯救”的人,是一种偶然。然而,我们在他的讲述中还是看到了个体能动性对个人命运的改写。这与他的反叛有关。
这种反叛首先是针对专断的父亲及他所代表的旧的家庭生活方式。父亲生前,他不愿意回家,父亲去世时,他也不愿意见他最后一面,甚至不曾参加父亲的葬礼。在父亲死后,他才觉得他可以完成回乡之旅。反叛家庭以及家庭所属阶级的行为方式和追求,是他的内核,是他最终能走出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撑。这一对家庭的反叛与逃离,与约翰·艾德迦·韦德曼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写的对家庭的逃离完全一致。
第二种反叛则是针对主流性规则的。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埃里蓬认为自己主动选择了不同于平民阶级的文化归属,以这种方式反抗平民阶级崇尚男子气概的价值观,以此“区隔”自己。因为不希望永远怀着羞耻与恐惧度过自己作为同性恋的一生,因此要反抗,要“将唾液变成玫瑰”“将语言攻击变成美丽的花环”,最终“将羞耻变成骄傲”,以此完成对正常标准和社会秩序的反叛。
他的回归是要试着去理解加诸在父母兄弟身上的结构性枷锁,是情感认同的回归,这与作为个体的他用自己的反叛脱离了既有的阶级归属,从而再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并不矛盾,本质上,他仍是创造自己命运“奇迹”的人。
阶级身份跨越及创造个体独特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埃里蓬是如何做到阶级身份跨越的?如何让主体觉醒并自觉抗争命运的枷锁?事实上,无论是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还是埃里蓬,他们共同改变命运的秘诀仍然是读书,是教育改变了他们的阶层身份和通往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虽然埃里蓬曾写及由于自己没有社会资源和家庭支撑,无法写博士论文,这让他的“文凭”“没有很大的价值”。然而,他后来偶然的记者生涯没有用上他这个“没用的”文凭以及为此读的书,还能算偶然遇到吗?答案是:不能。最终,还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当然,看起来还有他人生中的诸多“偶然”:比如在高中偶遇的同学男孩给予的友谊和“残忍”(同学的阶级属性带给埃里蓬的伤害),让埃里蓬改变了对阅读的兴趣和与文字的关系,开启他对既有人生路的挣扎与自觉思考。他后来开始广泛的读书和研究,在中学毕业会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显示萨特意义上的“主体的自由性”,摆脱了“历史决定论”。
但无论是高中的同学还是偶然结识的工作机会,都与作者读书生涯分不开,说到底,读书和思考是这一切偶然缘分的根基,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可能,就算遇到,也不会有机会。即便工作不如意,但是他能养活自己,进入到可以与知识分子相识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有可以写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了。
个体身份的跨越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改变了自己既定的人生道路,也带给家人新观念。比如,埃里蓬的父亲曾经无比厌恶同性恋,但在面对自己有出息的儿子出柜的事情上,他学会了宽容。
即使个人对既有道路的改变并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没有取得如布迪厄和埃里蓬一样的成就,没能真正跨越阶层身份,这种努力奋斗的探索之路本身仍是有意义的。萨特的那句“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理由支撑。不屈从命定的安排的一切努力和探索,让每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英雄,多么有趣!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