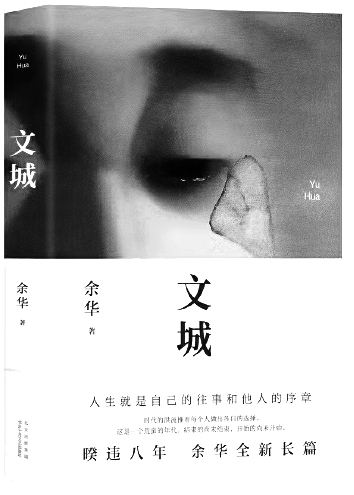编者按
《文城》是作家余华的全新长篇小说,正文以林祥福颠沛的寻妻际遇叙写时代背景下山河国土之悲,《文城·补》则以林祥福之妻小美的身世遭际书写个体尤其是遭受女德枷锁的女性生命的撕裂之痛。从《文城》中清末民初时期两个妇人的死亡,可以看出传统女德对女性自然人性和伦理属性的撕扯。正是有感于传统社会中有不少如此被害的沉默女性,辛亥革命时期,有进步人士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倒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吹起了性别观念时代转换的新风。
■ 尼莎
女德,或称妇德,是传统社会儒家伦理规约下的女子德性及其日常行为规范的指称。作为传统伦理秩序的内生物,女德思想发展至清末民初,形态已极其僵化,由其导致的情理冲突对女性生命与情感有着双重扼杀。通过余华长篇小说《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中清末民初时期两个妇人的死亡叙事,我们可以对此做一探讨。
妇人之死:德法统治下操行与性情的撕裂
《文城》由“正文”和“补”两部分构成。“正文”以林祥福颠沛的寻妻际遇叙写时代背景下山河国土之悲,“补”则以林祥福之妻小美的身世遭际书写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撕裂之痛。这一痛点内化在两位妇人的死亡叙写之中。
沈母是小美的婆婆,临终时曾不住呼唤小美而不得见,其死亡也由此遗憾化为深长叹息。作为小美的驱逐者,沈母的想念似不合逻辑。但小美被休实际出于沈母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的需要。得知小美擅自拿钱接济弟弟后,沈母本想小惩大诫,让其回娘家反省两月,而丈夫和儿子反常的维护成为她眼中三人伙同违抗自己的罪证,决定彻底休弃小美以巩固威信。但我们不能将小美被逐等同于沈母的厌恶之心。事实上,在一众女童中选定小美并将祖传的织补手艺传授给她,说明沈母对小美的认可与喜爱。小美成长过程中,沈母依照自己的样子教养她,耗费心血。在驱逐小美的早晨,沈母为小美准备好盘缠,这些隐藏着一位母亲真实的情感。
小美一路北上时,因饥贫假意委身林祥福,产女后选择不告而别。如果说对于沈母的叙写更重其服膺封建女教所显现的刻板,对小美则多从人性人情出发,描写其对两个男人的矛盾情感及身为人母对女儿的牵挂。而与沈母相比,小美死亡时内心情绪更加强烈。小美冻死在溪镇城隍阁祭天的仪式上,这一戏剧性描写使其死亡具有某种宗教式的赎罪及超脱意味。
女德之梏:从观念渗透至行为的牢网
从《文城》两位妇人的死亡中,可以看出传统女德对女性自然人性和伦理属性的撕扯。在从观念渗透至行为的牢网中,女性死亡的本质是相同的。
从空间上看,在万亩荡度过童年的小美,作为童养媳嫁入以织补为业的沈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织补”这门技艺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巫鸿在《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中曾引述《礼记》《女诫》等内容,指出早在汉代,“织”就与观念中的“女德”“女功”紧密联系。在儒家为女性设立的“四德”(德、言、容、功)伦理框架中,织作、裁衣等与纺织有关的活动,是能够通过“妇功”达到“德”的途径。
可以说,织补铺子是余华构筑的一个恰切的女性活动空间。沈母在这个空间里取代了父权社会中沈父本该扮演的角色,成为大家长。而沈母的衣橱作为沈家这一空间场域中的子空间,既是小美最初的向往,也是小美被惩罚的源头。新衣裳被收在沈母的衣橱里,衣橱恰似包括沈母和小美在内所有溪镇女人的宿命,“曾经有过明亮的朱红色,天长日久以后开始发黑。”小美因未经允许偷穿衣橱里的新衣服被沈母责罚,险遭休弃。逃过一劫后,她再未打开过衣橱。织补铺子、沈母房间与衣橱共同构成一个多层空间结构,成为埋藏情感的坟冢。
从时间上看,小美的成长史可以说是女德观念对传统女性的塑造史。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讲述了女德观念从先秦至明清,历经初创发展到僵化保守的过程。在女德观念发轫的先秦时期,女性尚无过多束缚。《周礼》中载“奔者不禁”,秦代始重贞洁。对贞洁的褒奖在汉代大为流行,刘向、班昭等人的著作使贞妇贤女形象广为流传。魏晋至隋唐时期,风雅女子及娼妓兴盛,贞洁观念淡薄。宋代新儒学大兴,为构建其社会伦理体系,将女德融入天理,从此历元明清三代,女德观念日益僵化,成为束缚女性身心的罗网。清末民初是女德教条化的巅峰,《女论语·学礼》章中曾言凡为女子应识礼数。若要知礼,须“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这是小美,也是沈母和多数中国女人的肖像画。当女德规范尚未上升为天理教条时,它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当它们内化为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枷锁时,便可作为刀戟,倏忽间夺去女人的一生。
情理之难:性别观念现代转化的必要
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女性一直在天理规范与自然人情的两难中挣扎。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曾提出“情本体”是中国传统乐感文化的核心,也是人生的根本。郭店竹简有“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苟以其情,虽过不恶”;孔孟所谓“汝安则为之”“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等伦理政治思想也皆从“情”出发。“情本体”强调人的自然情欲不可贬低,它虽承认理性凝聚的道德伦理,但反对将其神圣化以此压服人的感性生命。然而在当时,无论沈母、小美还是大部分中国女性,都处在女德神圣化的时代。如同张念在《女人的理想国》中所说,自宋代新儒家将女教细化为时刻修行的家范后,直至明清,“在道德践行的荣誉榜上,女前辈们以其强韧的意志力,将‘成为女人’当作一项绝对律令。”
事实上,相对于沈父和阿强,沈母和小美都处在较强势的位置。沈母取代了入赘的沈父,掌握着沈家的财产、人事等权力,在重返溪镇的小美和阿强两人之间,小美同样占据上风。在这迥异于当时性别结构的家庭关系中,为何两人依旧走向死亡呢?质言之,沈家内部的性别角色虽然对调了,但溪镇及整个中国的性别结构依然稳固,女德观念的强大影响力依然塑造着沈母与小美的社会性别属性。
正是有感于传统社会中有不少如此被害的沉默女性,辛亥革命时期的才女何震才在其主编的《天义报》中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倒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和习俗,团结起受男权传统压迫的女性群体为争取女性的尊严和权益而奋斗。其《女子复权会简章》一文,指明女子道德应为“耐苦、冒险、知耻、贵公、正身”,亦可以说吹起了性别观念时代转换的新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视野下儒家女性观的现代性转化——以清末民初文学作品为样本的分析”(20XNH14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