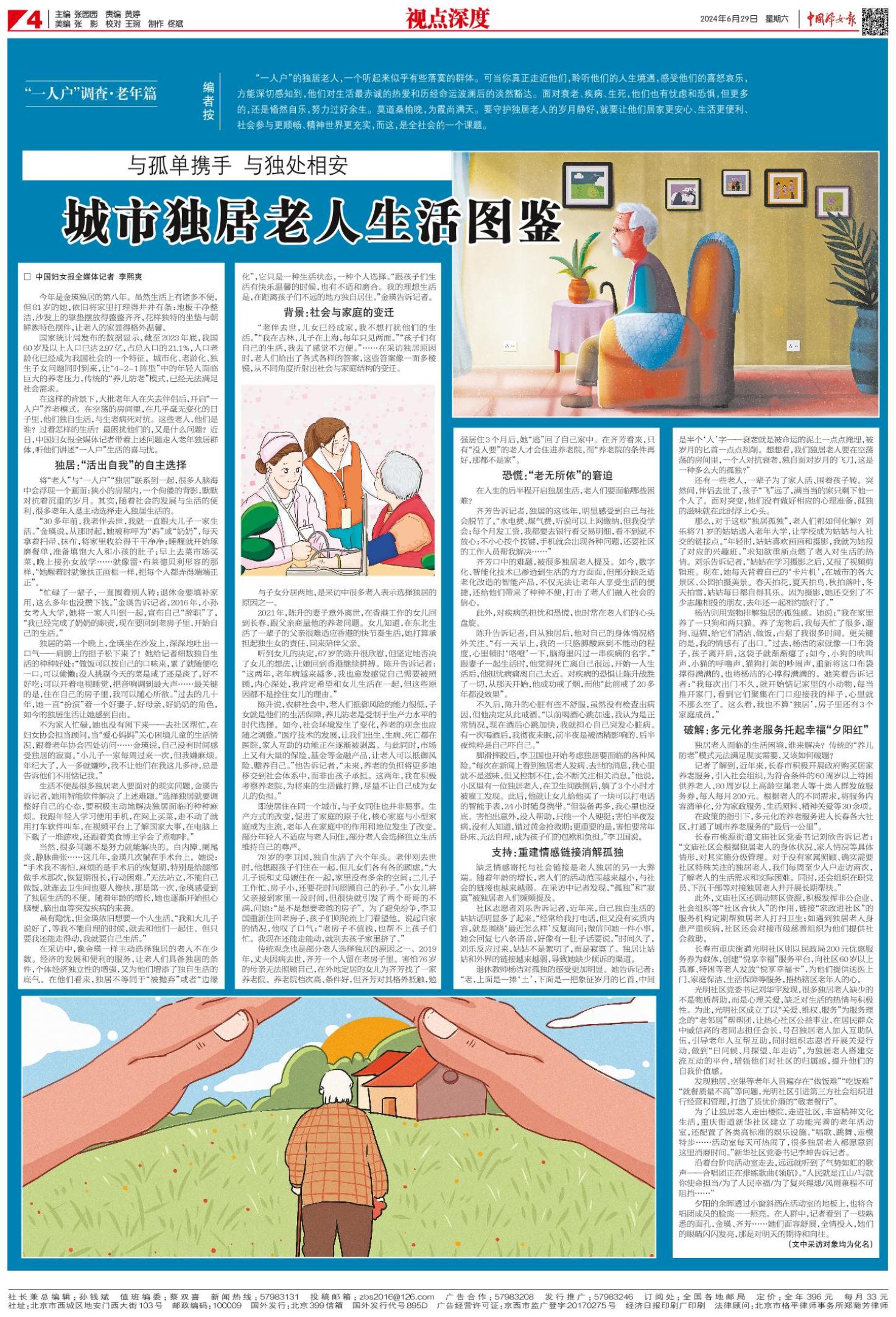编者按
“一人户”的独居老人,一个听起来似乎有些落寞的群体。可当你真正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人生境遇,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方能深切感知到,他们对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和历经命运波澜后的淡然豁达。面对衰老、疾病、生死,他们也有忧虑和恐惧,但更多的,还是翛然自乐,努力过好余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要守护独居老人的岁月静好,就要让他们居家更安心、生活更便利、社会参与更顺畅、精神世界更充实,而这,是全社会的一个课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熙爽
今年是金瑛独居的第八年。虽然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但81岁的她,依旧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地板干净整洁,沙发上的靠垫摆放得整整齐齐,花样独特的坐垫与朝鲜族特色摆件,让老人的家显得格外温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城市化、老龄化、独生子女问题同时到来,让“4-2-1阵型”中的年轻人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老年人在失去伴侣后,开启“一人户”养老模式。在空荡的房间里,在几乎毫无变化的日子里,他们独自生活,与生老病死对抗。这些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最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问题?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带着上述问题走入老年独居群体,听他们讲述“一人户”生活的喜与忧。
独居:“活出自我”的自主选择
将“老人”与“一人户”“独居”联系到一起,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一个画面:狭小的房屋内,一个佝偻的背影,默默对抗着沉重的岁月。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活的便利,很多老年人是主动选择走入独居生活的。
“30多年前,我老伴去世,我就一直跟大儿子一家生活。”金瑛说,从那时起,她被称呼为“妈”或“奶奶”,每天拿着扫帚、抹布,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睡醒就开始琢磨餐单,准备填饱大人和小孩的肚子;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晚上接孙女放学……就像雷·布莱德贝利形容的那样,“她醒着时就像扶正画框一样,把每个人都弄得端端正正”。
“忙碌了一辈子,一直围着别人转;退休金要填补家用,这么多年也没攒下钱。”金瑛告诉记者,2016年,小孙女考入大学,她将一家人叫到一起,宣布自己“辞职”了,“我已经完成了奶奶的职责,现在要回到老房子里,开始自己的生活。”
独居的第一个晚上,金瑛坐在沙发上,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肩膀上的担子松下来了!她给记者细数独自生活的种种好处:“做饭可以按自己的口味来,累了就随便吃一口,可以偷懒;没人挑剔今天的菜是咸了还是淡了,好不好吃;可以开着电视睡觉,把音响调到最大声……最关键的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可以随心所欲。”过去的几十年,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奶奶的角色,如今的独居生活让她感到自由。
不为家人忙碌,她也没有闲下来——去社区帮忙,在妇女协会担当顾问,当“爱心妈妈”关心困境儿童的生活情况,跟着老年协会四处访问……金瑛说,自己没有时间感受独居的寂寞。“小儿子一家每周过来一次,但我嫌麻烦。年纪大了,人一多就嫌吵,我不让他们在我这儿多待,总是告诉他们不用惦记我。”
生活不便是很多独居老人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金瑛告诉记者,她用智能软件解决了上述难题。“选择独居就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积极主动地解决独居面临的种种麻烦。我跟年轻人学习使用手机,在网上买菜,走不动了就用打车软件叫车,在视频平台上了解国家大事,在电脑上下载了一堆游戏,还跟着美食博主学会了煮咖啡。”
当然,很多问题不是努力就能解决的。白内障、阑尾炎、静脉曲张……这几年,金瑛几次躺在手术台上。她说:“手术我不害怕,麻烦的是手术后的恢复期,特别是给腿部做手术那次,恢复期很长,行动困难。”无法站立,不能自己做饭,就连去卫生间也要人搀扶,那是第一次,金瑛感受到了独居生活的不便。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逐渐开始担心脑梗、脑出血等突发疾病的来袭。
虽有隐忧,但金瑛依旧想要一个人生活。“我和大儿子说好了,等我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去和他们一起住。但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要自己生活。”
在采访中,像金瑛一样主动选择独居的老人不在少数。经济的发展和便利的服务,让老人们具备独居的条件,个体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又为他们增添了独自生活的底气。在他们看来,独居不等同于“被抛弃”或者“边缘化”,它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个人选择。“跟孩子们生活有快乐温馨的时候,也有不适和磨合。我的理想生活是,在距离孩子们不远的地方独自居住。”金瑛告诉记者。
背景:社会与家庭的变迁
“老伴去世,儿女已经成家,我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我在吉林,儿子在上海,每年只见两面。”“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我去了感觉不方便。”……在采访独居原因时,老人们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这些答案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变迁。
与子女分居两地,是采访中很多老人表示选择独居的原因之一。
2021年,陈升的妻子意外离世,在香港工作的女儿回到长春,跟父亲商量他的养老问题。女儿知道,在东北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很难适应香港的快节奏生活,她打算承担起独生女的责任,回来陪伴父亲。
听到女儿的决定,67岁的陈升很欣慰,但坚定地否决了女儿的想法,让她回到香港继续拼搏。陈升告诉记者:“这两年,老年病越来越多,我也愈发感觉自己需要被照顾,内心深处,我肯定希望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但这些原因都不是拴住女儿的理由。”
陈升说,农耕社会中,老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子女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养儿防老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的时代选择。如今,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养老的观念也应随之调整。“医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出生、生病、死亡都在医院,家人互助的功能正在逐渐被剥离。与此同时,市场上又有大量的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让老人可以抵御风险、赡养自己。”他告诉记者,“未来,养老的负担将更多地移交到社会体系中,而非由孩子承担。这两年,我在积极考察养老院,为将来的生活做打算,尽量不让自己成为女儿的负担。”
即使居住在同一个城市,与子女同住也并非易事。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家庭的原子化,核心家庭与小型家庭成为主流,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改变。部分年轻人不适应与老人同住,部分老人会选择独立生活维持自己的尊严。
78岁的李卫国,独自生活了六个年头。老伴刚去世时,他想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但儿女们各有各的顾虑。“大儿子说和丈母娘住在一起,家里没有多余的空间;二儿子工作忙、房子小,还要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孙子。”小女儿将父亲接到家里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引发了两个哥哥的不满,问她:“是不是想要老爸的房子”。为了避免纷争,李卫国重新住回老房子,孩子们则轮流上门看望他。说起自家的情况,他叹了口气:“老房子不值钱,也帮不上孩子们忙。我现在还能走能动,就别去孩子家里挤了。”
传统观念也是部分老人选择独居的原因之一。2019年,丈夫因病去世,齐芳一个人留在老房子里。害怕76岁的母亲无法照顾自己,在外地定居的女儿为齐芳找了一家养老院。养老院档次高、条件好,但齐芳对其格外抵触,勉强居住3个月后,她“逃”回了自己家中。在齐芳看来,只有“没人要”的老人才会住进养老院,而“养老院的条件再好,那都不是家”。
恐慌:“老无所依”的窘迫
在人生的后半程开启独居生活,老人们要面临哪些困难?
齐芳告诉记者,独居的这些年,明显感受到自己与社会脱节了。“水电费、煤气费,听说可以上网缴纳,但我没学会;每个月发工资,我都要去银行看交易明细,看不到就不放心;不小心按个按键,手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要社区的工作人员帮我解决……”
齐芳口中的难题,被很多独居老人提及。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部分缺乏适老化改造的智能产品,不仅无法让老年人享受生活的便捷,还给他们带来了种种不便,打击了老人们融入社会的信心。
此外,对疾病的担忧和恐慌,也时常在老人们的心头盘旋。
陈升告诉记者,自从独居后,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格外关注。“有一天早上,我的一只胳膊酸麻到不能动的程度,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脑海里闪过一串疾病的名字。”跟妻子一起生活时,他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远,开始一人生活后,他担忧病痛离自己太近。对疾病的恐惧让陈升战胜了一切,从那天开始,他成功戒了烟,而他“此前戒了20多年都没效果”。
不久后,陈升的心脏有些不舒服,虽然没有检查出病因,但他决定从此戒酒。“以前喝酒心跳加速,我认为是正常情况,现在酒后心跳加快,我就担心自己突发心脏病。有一次喝酒后,我彻夜未眠,前半夜是被酒精影响的,后半夜纯粹是自己吓自己。”
脚滑摔跤后,李卫国也开始考虑独居要面临的各种风险。“每次在新闻上看到独居老人发病、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但又控制不住,会不断关注相关消息。”他说,小区里有一位独居老人,在卫生间跌倒后,躺了3个小时才被雇工发现。此后,他就让女儿给他买了一块可以打电话的智能手表,24小时随身携带。“但装备再多,我心里也没底。害怕出意外,没人帮助,只能一个人硬挺;害怕半夜发病,没有人知道,错过黄金抢救期;更重要的是,害怕要常年卧床、无法自理,成为孩子们的包袱和负担。”李卫国说。
支持:重建情感链接消解孤独
缺乏情感寄托与社会链接是老人独居的另一大弊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与社会的链接也越来越弱。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孤独”和“寂寞”被独居老人们频频提及。
社区志愿者刘乐告诉记者,近年来,自己独自生活的姑姑话明显多了起来。“经常给我打电话,但又没有实质内容,就是围绕‘最近怎么样’反复询问;微信问她一件小事,她会回复七八条语音,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时间久了,刘乐反应过来,姑姑不是絮叨了,而是寂寞了。独居让姑姑和外界的链接越来越弱,导致她缺少倾诉的渠道。
退休教师杨洁对孤独的感受更加明显。她告诉记者:“老,上面是一捧‘土’,下面是一把象征岁月的匕首,中间是半个‘人’字——衰老就是被命运的泥土一点点掩埋,被岁月的匕首一点点刮削。想想看,我们独居老人要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人对抗衰老,独自面对岁月的飞刀,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孤独?”
还有一些老人,一辈子为了家人活、围着孩子转。突然间,伴侣去世了,孩子“飞”远了,满当当的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面对突变,他们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孤独的滋味就在此时浮上心头。
那么,对于这些“独居孤独”,老人们都如何化解?刘乐将71岁的姑姑送入老年大学,让学校成为姑姑与人社交的链接点。“年轻时,姑姑喜欢画画和摄影,我就为她报了对应的兴趣班。”求知欲重新点燃了老人对生活的热情。刘乐告诉记者,“姑姑在学习摄影之后,又报了视频剪辑班。现在,她每天背着自己的‘卡片机’,在城市的各大景区、公园拍摄美景。春天拍花,夏天拍鸟,秋拍落叶,冬天拍雪,姑姑每日都自得其乐。因为摄影,她还交到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年还一起相约旅行了。”
杨洁则用宠物排解独居的孤独感。她说:“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狗和两只猫。养了宠物后,我每天忙了很多,遛狗、逗猫,给它们清洁、做饭,占据了我很多时间。更关键的是,我的情感有了出口。”过去,杨洁的家就像一口布袋子,孩子离开后,这袋子就渐渐瘪了;如今,小狗的吠叫声、小猫的呼噜声、猫狗打架的吵闹声,重新将这口布袋撑得满满的,也将杨洁的心撑得满满的。她笑着告诉记者:“我每次出门不久,就开始惦记家里的小动物,每当推开家门,看到它们聚集在门口迎接我的样子,心里就不那么空了。这么看,我也不算‘独居’,房子里还有3个家庭成员。”
破解:多元化养老服务托起幸福“夕阳红”
独居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谁来解决?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又该如何破题?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长春市积极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引入社会组织,为符合条件的60周岁以上特困供养老人、80周岁以上高龄空巢老人等十类人群发放服务券,每人每月200元。根据老人的不同需求,将服务内容清单化,分为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精神关爱等30余项。
在政策的指引下,多元化的养老服务进入长春各大社区,打通了城市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长春市桃源街道文庙社区党委书记刘欣告诉记者:“文庙社区会根据独居老人的身体状况、家人情况等具体情形,对其实施分级管理。对于没有家属照顾、确实需要社区特殊关注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周至少入户走访两次,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和实际困难。同时,还会组织在职党员、下沉干部等对接独居老人并开展长期帮扶。”
此外,文庙社区还调动辖区资源,积极发挥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社区合伙人”的作用,链接“家政进社区”的服务机构定期帮独居老人打扫卫生;如遇到独居老人身患严重疾病,社区还会对接市级慈善组织为他们提供社会救助。
长春市重庆街道光明社区则以民政局200元优惠服务券为载体,创建“悦享幸福”服务平台,向社区60岁以上孤寡、特困等老人发放“悦享幸福卡”,为他们提供送医上门、家庭保洁、生活保障等服务,捂热辖区老年人的心。
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华宇发现,很多独居老人缺少的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心理关爱,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与积极性。为此,光明社区成立了以“关爱、维权、服务”为服务理念的“老邻居”帮帮团,让热心社区公益事业、在居民群众中威信高的老同志担任会长,号召独居老人加入互助队伍,引导老年人互帮互助,同时组织志愿者开展关爱行动,做到“日问候、月探望、年走访”,为独居老人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发现独居、空巢等老年人普遍存在“做饭难”“吃饭难”“就餐质量不高”等问题,光明社区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经营和管理,打造了质优价廉的“敬老餐厅”。
为了让独居老人走出楼院,走进社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建立了功能完善的老年活动室,还配置了各类高标准的娱乐设施。“唱歌、跳舞、走模特步……活动室每天可热闹了,很多独居老人都愿意到这里消磨时间。”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李坤告诉记者。
沿着台阶向活动室走去,远远就听到了气势如虹的歌声——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领航》。“人民就是江山/写就你使命担当/为了人民幸福/为了复兴理想/风雨兼程不可阻挡……”
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斜洒在活动室的地板上,也将合唱团成员的脸庞一一照亮。在人群中,记者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金瑛、齐芳……她们面容舒展,全情投入,她们的眼睛闪闪发亮,那是对明天的期待和向往。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