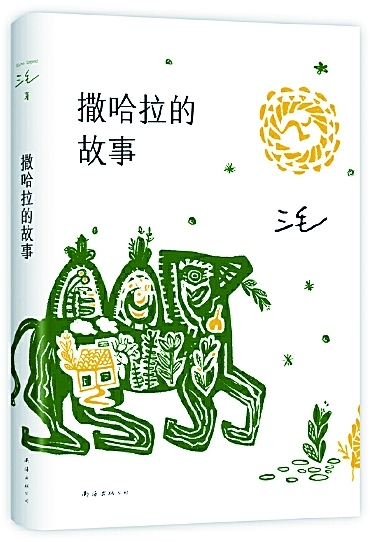
我们无须复刻她的撒哈拉,却可汲取她将生活根植于自由沃土的智慧——在庸常琐碎中葆有飞扬的姿态,于尘沙弥漫处活出优雅的从容。
■ 李星涛
13岁那年的暑假,我在姐姐的书架上偶然发现了一本封面斑驳的《撒哈拉的故事》。翻开后,《沙漠中的饭店》一文瞬间攫住了我——当三毛戏称粉丝为“春雨”,把猪肉干包装成“喉片”逗弄丈夫荷西时,躺在吱呀作响的竹席上的我,忍不住放声大笑。窗外皖北小城的阵阵蝉鸣,仿佛与撒哈拉漫天的黄沙在眼前交织,悄悄点燃了我对遥远世界的炽热憧憬。多年后重读,当目光触及《哑奴》中善良的奴隶被强行拖走的无助场景,或是《哭泣的骆驼》里沙伊达血染沙海的悲怆结局时,泪珠无声滚落。三毛的文字依旧如昨,只是解读它们的目光,早已被时光重新校准。
对于三毛而言,这次撒哈拉之旅,是她在梦中一场蓄谋已久的灵魂奔赴。年少时,我只把它看作是三毛的浪漫和潇洒,对她以“前世的乡愁”来形容那片荒原不以为然,直到我25岁那年经历了一场失恋,自愿远赴北疆支教,在高原缺氧的寒夜里再次翻开这本书时,才真正体会到那份召唤蕴含的悲苦。1974年,三毛决然离开中国台北,舍弃安稳的职业,将自己投身于贫瘠之地时,那并非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而是源于灵魂深处的自我放逐。“撒哈拉沙漠,像那无法言说的梦中情人,是萦绕于前世记忆里的乡愁。”再次读到这句话时,我竟然感同身受,虽然我面前是陌生的北疆雪山,可内心里,这番景象却像是我等候多时的老友,那种辽阔和沉静,已在我心里拓展开另一种生活。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读懂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是撕开童话面纱后的真实人间。在《沙漠观浴记》中,当地妇女用石子刮下混合乳汁的黑色污垢喂给婴儿的画面,曾让年少的我几欲作呕,差点合上书页;《芳邻》中邻居们理直气壮地“借”走一切物品,甚至说出“你伤害了我的骄傲”时,也曾让我对那片土地心生疏离。直到在柬埔寨支教,亲眼看见村民用浑浊的水煮食,却毫不犹豫地将仅存的洁净米粮捧给客人,我才恍然领悟三毛文字背后的深意——她以包容之心凝视着横亘的文化沟壑,记录着种种荒诞,却始终怀抱悲悯。撒哈拉威人的行为准则深深植根于严酷的生存现实,正如哑奴在被强行带走前,仍偷偷为三毛洗净并摆好生菜叶。这份跨越阶层、地域与文化的温暖,恰是人性在绝境中绽放的坚韧之花。
三毛是坚强的,“安身立命”这个成语所包含的人生意义中,她重点选取的是“立命”的部分。她的非凡之处,在于“立命”之后,又能用“立命”的营养反哺“安身”的生活,从而将平凡的日子淬炼成一首首生动的诗。《荒山之夜》里,她与丈夫荷西寻找化石时,曾遭遇一段惊险历程:荷西深夜探路,深陷泥潭,命悬一线。她智斗流氓,绝处逢生。情节跌宕,如波浪汹涌。更撼动心灵的是,脱险后她和荷西简短的对话:“还要化石吗?”“要。你呢?”“我更要。明天下午再来?”这种直面死亡的浪漫,是对生活坚定的挚爱,更是来自灵魂深处相互懂得的爱情之火。1995年,我组建家庭后,再读《白手成家》,却被另一种力量深深震撼:三毛用废弃的棺材板打造沙发,拾来破轮胎制成坐垫,把简陋的铁皮小屋变成了“沙漠中最美丽的家”。当我在都市狭小的出租屋里为空间局促而焦虑时,三毛的实践如一道光——生活的美学从不仰赖物质的丰俭,而在于心灵是否拥有开垦荒原的创造力量。
撒哈拉是三毛的精神坐标,但她流浪的脚步从未在此停驻。《万水千山走遍》中,秘鲁的印第安古城遗迹、玻利维亚的广袤高原湖泊、墨西哥的葱郁雨林,次第在她笔下铺陈开来。中南美洲的漫游,是她走出荷西骤然离世阴影的自我疗愈之旅。当我漫步在北疆的街头,遇见书中描述般兜售巫术用品的艾马拉族妇人,瞬间理解了三毛所言“飞蛾扑火时,一定极快乐”——流浪于她,不仅是生存的姿态,更是向生命本源的深情回归。
年轻时向往三毛笔下“橄榄树”般的人生,以为漂泊即是浪漫的全部。直到在异国他乡亲历盗窃、疾病与蚀骨的孤寂,才真正明白自由背后沉重的代价。《撒哈拉的故事》里早有伏笔:当荷西失业,两人捕鱼维生却血本无归时,三毛笑着宣告“我们破产了”,随即用卖不掉的鱼煮汤庆祝。这种在苦涩中酿造甘甜的精神,清晰地勾勒出从《雨季不再来》中的“二毛”蜕变为“三毛”的轨迹。人到中年再读,更被她后期的《送你一匹马》《温柔的夜》所震撼——此时,她的文字洗尽铅华,流露出对人间烟火更深沉的眷恋。她为自闭症儿童耐心授课,深夜执笔回复读者来信,在演讲中拥抱素昧平生却泪流满面的陌生人。这位永恒的流浪者,最终停泊在对尘世万物的深情之中。正如她的箴言:“活着,就是在沙漠里寻觅海市蜃楼般的欢愉,然后让希望之花在荒芜之上粲然绽放。”
如今的世界被算法与效率所裹挟,年轻的心灵常被各种“人设”与标签所定义,三毛的撒哈拉精神恰似荒漠甘泉。当信息茧房将我们的目光变得狭窄,她示范了如何以开放的视角在文化褶皱里发掘趣味;当碎片信息割裂着深度思考,她证明了唯有将生命投入真切体验,才能孕育出丰厚的生命文本。她的自由并非逃离,而是以全然敞开的心,去拥抱每一种生命形态,无论阳春白雪,抑或烟火人间。
合上书本,三毛的叩问仍在心间回响:“倘若有来生,愿化为一棵树。一半在尘土中安然沉淀,一半在风中自在飞扬。”我们无须复刻她的撒哈拉,却可汲取她将生活根植于自由沃土的智慧——在庸常琐碎中葆有飞扬的姿态,于尘沙弥漫处活出优雅的从容。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暑假我完成了三年的援疆任务。当我背起行李和三毛的十几本书离开宿舍的瞬间,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化成了北疆的一棵树,在北疆走过的路已经化成茂盛的枝条,在北疆留下的脚印已化作碧绿的树叶,而那枝头上最美的果实则化作了一颗心脏,它正向我的全身泵去鲜红的、饱含生命力的血液,日夜涌动。那是我前世的乡愁,也是我今生今世灵魂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