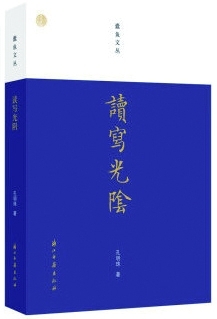唯有无比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工笔画般地细描一箪食一瓢饮;写小菜的文章也未见得就铺排不出如磐的风雨。只是,与不少被岁月捶打过从而只看得见乌云的人不一样,孔明珠更愿意传递给读者的,是生活中的暖意。
■ 吴玫
被我们昵称为明珠姐姐的孔明珠,嘱我阅读她的新作《读写光阴》时,顺便寄来了一年前出版的《井荻居酒屋》。随书来的,还有一张明信片,三言两语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自卑作祟,怕被人贴上写小菜标签”。掩口暗笑之后,也觉得奇怪。将孔明珠业已出版的书籍摞在一起,它们是《月明珠还》《上海妹妹》《亲爱的咪咪噜》《孔娘子厨房》《烟火气》《煮物之味》以及我手边的这两本,等等。非得要以所写内容分类作家的话,孔明珠也只能算是半个“写小菜”的作家,怎么一说起她就让读者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了厨房?我特意翻出《孔娘子厨房》和《煮物之味》重温了一下,我想我找到答案了:总是琢磨着把平常食材烧煮成家庭餐桌上的至味的孔明珠,还乐意将整个过程白纸黑字并配上美图分享给大家,这好比打开了她家厨房开在后弄堂的小门,对想要了解那扇门里上海味道的读者而言,是一种很有黏附力的诱惑。
这种诱惑,被孔明珠延续到了《井荻居酒屋》里。按照出版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说法,《井荻居酒屋》是孔明珠早年旅居日本东京、在井荻居酒屋打工时旁观到的平凡故事。这个总结不无道理,被孔明珠收入书里的十个故事,除了首篇写的是居酒屋老板娘桑幸子的故事外,主角均为井荻居酒屋的客人或打工者,他们或如居酒屋老板修整过准备投入“炖牛杂烩”的萝卜,已被世态炎凉修理成了炖圆形却依然无法汇入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或是被东京的灯红酒绿迷了眼,打算从居酒屋出发闯荡出一番新天地的后生小子,他们的快意和恩仇,被孔明珠落笔一写,虽然苦涩,但配以居酒屋老板特别烹制的炸鸡块、土豆炖肉、腌烤青花鱼等美味佳肴后,一本《井荻居酒屋》,就像著名民谣歌手周云蓬在序言里概述的那样,“读着读着,你就饿了,肚子咕咕叫,口水潺潺流,那恭喜你,读出了这本书的好处。”这就是孔明珠写的“小菜”,悲辛之余总用一口好吃的,让读者觉得生活还是有滋味的。
只有心底敞亮的人,才会这样再现生活。
我第一次见到孔明珠,是在一个炎夏的午后,那时,她是《交际与口才》杂志的主编。《交际与口才》与我所在的报社合作一个项目,双方相约见面商讨细节。高温酷暑,谁都不愿在大太阳底下来回奔波,姿态颇高的《交际与口才》二话没说就答应来我们报社。可谁也没想到,来的竟然是杂志的主编,更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孔明珠居然是骑着自行车来的。我在办公楼门外等到的孔明珠,已经大汗淋漓。当她摘下遮阳帽一下紧接一下扇着风时,我看见她涂着非常好看的口红,被汗水濡湿的脸上满是笑容。
所以,机缘巧合地与友人聊起早年在日本陪读的那些日子,她会过滤掉不快乐的部分,这就给了我们一种错觉,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井荻居酒屋》“出卖”了她,试想,若没有相同的经历,孔明珠怎么能如此体己地共情在井荻居酒屋进进出出的客人和打工人?至于很少言及彼时的寂寞和艰苦,在井荻居酒屋里打工的那些日子让她愈发相信,一个喜欢美食的人,哪怕被狰狞的生活打趴在了地上,也能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向阳而行,《台湾新嫁娘秀丽》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从台湾远嫁到东京的秀丽,明明已经被不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和怎么也忘不了的家乡撕扯得粉身碎骨,但孔明珠就是不想让读者记住的秀丽总在悲悲切切,就在此文的附录《炸鸡块》里记录了秀丽吃炸鸡块的样子:“老公不吃那玩意儿,她就一个人吃,像一个少女,嚼得满嘴漏油……” 由此得见,孔明珠是打定了主意要为自己笔下的人和事,添上温暖色。食物,在将家庭餐桌拿捏得自在自如的孔明珠看来,是比一整本色卡都靠谱的暖色调。
这种写法,在《读写光阴》中尤为显见。
由“纸相遇”“梦相见”和“情相系” 等三辑汇集而成的《读写光阴》,书名就已“泄露天机”,收拢的都是孔明珠关于读与写的记忆。其中,“纸相遇”是孔明珠读罢一本本书后留在心里的挥之不去的感慨;“梦相见”是与书人书事相关的孔明珠的往事回忆;“情相系”则是孔明珠步履所到之处兴之所至的笔下留痕,有意思的是,这一辑中倒有半数文章的标题里嵌入了食物或餐厅的名称,可见,孔明珠丝毫也不在意被人称作“写小菜”的作者。
正因为此,那篇回忆她的父亲,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学史家孔另境先生的文章,孔明珠要以“上海蜜梨”题名?
孔另境,浙江桐乡乌镇人。早年投身革命,1924年起发表作品。孔另境一生经历坎坷,但始终不坠青云之志,为中国新文化的传扬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父亲,完全可以写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怀念他纪念他,孔明珠却以上海蜜梨、天津鸭梨、新疆香梨为经线,密密缝入父亲在那段特殊时期的遭遇,“编织”出的《上海蜜梨》篇幅不大,但肌理格外密实。孔明珠写道:“那时学校不太上课,我在家经常与爸爸相对枯坐,聊些生活琐事。爸爸听我谈论从弄堂邻居家学来的勤俭持家方法,没明说,但我知道面对现实,他心气已远不如以往,我买回挖去烂洞的梨回家,他也不会怪我……”我们读到了一个荒唐年代的侧影,也读到了阴影之下一位革命老人的无奈和不甘,以及老少两代孔家人面对不公时所做的力所能及的抗争。
就这样,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由一写起食物来就满腹情怀的孔明珠娓娓道来,懂得的读者自然能读到其中的微言大义。
所以,孔明珠怎么会在意被定位成写小菜的作家?她心里非常笃定,唯有无比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工笔画一般地细描一箪食一瓢饮;写小菜的文章也未见得就铺排不出如磐的风雨。只是,与不少被岁月捶打过从而只看得见乌云的人不一样,孔明珠更愿意传递给读者的,是生活中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