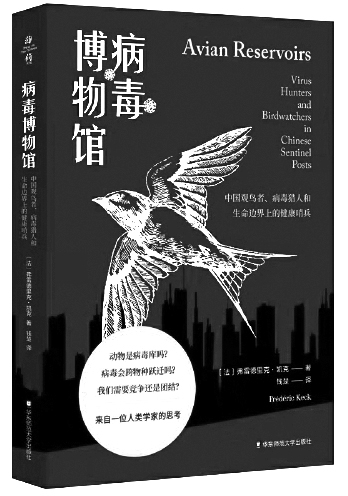《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病毒猎人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的新作,涉及病毒学、鸟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概念。本文作者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视角和单一学科的范畴,超越了片面和孤立,让我们通过反思人类和动物、文明和自然的关系,甚至通过动物的视角,来理解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应对措施。
■ 赵忻怡
《病毒博物馆:中国观鸟者、病毒猎人和生命边界上的健康哨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以下称为“凯克”)的新作,涉及病毒学、鸟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概念。
在这本书中,凯克以三个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民族志调查为基础,联系人类学理论,阐释人类处理人畜共患病的不同措施,分析公共卫生危机中人类、鸟类和病毒的相互关系,探讨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如何在应对禽流感的措施中被重塑。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理论分析,引出“准备”的概念及其对于人畜共患病防控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三地“准备”措施的实践,分析其中人类、鸟类和病毒之间紧密又复杂的关系。
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上的传染病
刚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理论可能会让非社会学或人类学专业的读者有点“烧脑”。然而这就是凯克的风格——理论性很强。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凯克讨论了人类学是如何通过群体的视角来看待人畜共患疾病的。凯克回顾了几位社会学、人类学大师——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涂尔干和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等对于公共卫生历史上几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的解读,反思了几种主要的管理和应对传染病的方式(也是本书的关键概念),即——预防、防备、准备。
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以一位农夫抱怨对于“口蹄疫”的公共政策作为开篇(虽然实际上斯宾塞混淆了口蹄疫和牛瘟)。他认为只有国家能通过统计数据组织“预防”工作,扑杀被感染的动物是“预防”的具体策略,是国家采取的必要干预措施。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提到了巴斯德的天花实验,指出疾病的存在并非毫无益处,接种天花疫苗可以提高生存几率,所以和人们获得的免疫相比,疾病造成的损害微不足道。他认为国家的干预不是通过法律强迫农夫处理所有的牲畜,而是通过免疫规范,对特定的动物进行接种。疫苗接种是一种治理技术,属于“防备”的具体策略。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从弗利部落中“食人者”的角度审视疯牛病,认为疯牛病提醒人类应该警惕工业化养殖,人和动物的关系应该向“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回归——因为猎人通常会从动物的视角思考。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人类可以用动物作为警告信号进行监测,为将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
鸟类相当于人类研究灭绝趋势的“指示物种”
凯克采用民族志方法,通过2007-2013年间在三个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实地研究,分别描述“岗哨(sentinels)”“模拟(simulation)”和“囤积(stockpiling)”这三种“准备”技术,分析其如何在三地禽流感防控中发挥作用,探讨“准备”技术中的病毒、鸟类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在中国香港,微生物学家、兽医、观鸟者和公共卫生部门通过不同层面的“岗哨”发出预警信号。在新加坡,微生物学家和公共卫生部门通过计算机程序的“桌面模拟”来模拟病毒的起源;通过扑杀家禽或疏散病人的“情境模拟”来增加大众和医务人员对于禽流感的体验。在中国台湾,公共卫生部门“囤积”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来为可能的威胁做准备。
凯克认为,微生物学家和观鸟者从动物的视角,通过不同层面的“岗哨”和动物交流。在养殖场层面,“哨兵鸡”发出预警信号。人们像狩猎社会的猎人一样,从动物的角度思考,把“哨兵鸡”看作帮助人类监控病毒、和人类一同抗疫的“士兵”,而不是纯粹的商品或生物。在环境层面,旗舰物种或指示物种发出信号。观鸟者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取代了弓箭和步枪,从鸟类的视角看世界。他们意识到,鸟类没有飞走而配合拍摄,是希望换取自然保护区对自己的庇护。而现代社会的自然保护区实际上也是监控生物多样性的“博物馆”。鸟类相当于人类研究灭绝趋势的“指示物种”,他们被生物学家观察、分类、监控,就像文物在博物馆里被保存一样。
从动物视角理解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应对措施
凯克的这本书,让我们反思人类文明发展、人类和动物的相处模式、以及病毒传播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和动物之间相处模式的改变,会增加流行病暴发风险。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所提及,从狩猎社会到畜牧社会的转变,动物作为“家畜”进入了人类居住场所。人类喂养动物,而动物回报给人类肉、蛋、奶等产品,或作为人类的交通工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礼物”——病毒传播的风险。
到了现代社会,工业化养殖、森林破坏、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因素减少了生物多样性,继而增加了病毒从一种动物直接转移到另一种动物的风险。另一方面,人类用来减少这些风险的措施,包括大规模扑杀家禽的“预防”措施,或是使用哨兵鸡的“准备”措施,也会改变人类与动物的相处模式。在中国香港的实践中,微生物学家和观鸟者又重新回归成为狩猎-采集社会的“狩猎-采集者”,通过“岗哨”,从动物的视角和动物进行交流。也许我们应当意识到,人类并不是生态系统的主导,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和其他物种互相依存。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诠释》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即使是对同一事物,不同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果能拥有站在他者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凯克新作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视角和单一学科的范畴,超越了片面和孤立,让我们通过反思人类和动物、文明和自然的关系,甚至通过动物的视角,来理解人畜共患传染病和应对措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