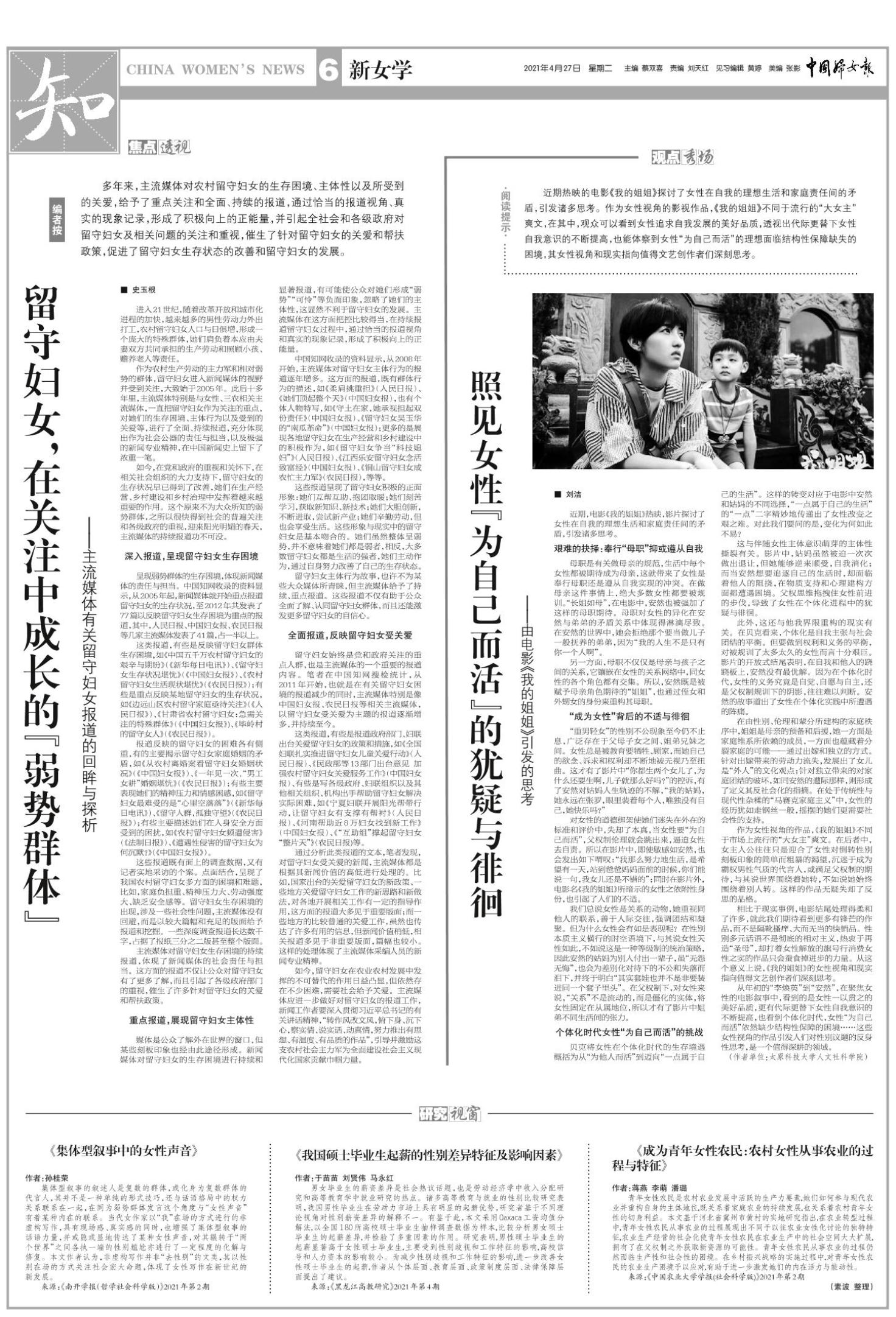·阅读提示·
近期热映的电影《我的姐姐》探讨了女性在自我的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间的矛盾,引发诸多思考。作为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我的姐姐》不同于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其中,观众可以看到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美好品质,透视出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也能体察到女性“为自己而活”的理想面临结构性保障缺失的困境,其女性视角和现实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 刘洁
近期,电影《我的姐姐》热映,影片探讨了女性在自我的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间的矛盾,引发诸多思考。
艰难的抉择:奉行“母职”抑或遵从自我
母职是有关做母亲的规范,生活中每个女性都被期待成为母亲,这就带来了女性是奉行母职还是遵从自我实现的冲突。在做母亲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女性都要被规训。“长姐如母”,在电影中,安然也被强加了这样的母职期待。母职对女性的异化在安然与弟弟的矛盾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安然的世界中,她会拒绝那个要当做儿子一般抚养的弟弟,因为“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
另一方面,母职不仅仅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它镶嵌在女性的关系网络中,同女性的各个角色都有交集。所以,安然既是被赋予母亲角色期待的“姐姐”,也通过侄女和外甥女的身份来重构其母职。
“成为女性”背后的不适与徘徊
“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公现象至今仍不止息,广泛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姐弟兄妹之间。女性总是被教育要牺牲、顾家,而她自己的欲念、诉求和权利却不断地被无视乃至扭曲。这才有了影片中“你都生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的控诉,有了安然对姑妈人生轨迹的不解,“我的姑妈,她永远在张罗,眼里装着每个人,唯独没有自己,她快乐吗?”
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使她们迷失在外在的标准和评价中,失却了本真,当女性要“为自己而活”,父权制伦理就会跳出来,逼迫女性去自责。所以在影片中,即使敏感如安然,也会发出如下喟叹:“我那么努力地生活,是希望有一天,站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你们能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同时在影片外,电影名《我的姐姐》所暗示的女性之依附性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不适。
我们总说女性是关系的动物,她重视同他人的联系,善于人际交往,强调团结和凝聚。但为什么女性会有如是表现呢?在性别本质主义横行的时空语境下,与其说女性天性如此,不如说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统治策略,因此安然的姑妈为别人付出一辈子,虽“无怨无悔”,也会为差别化对待下的不公和失落而泪下,并终于明白“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在父权制下,对女性来说,“关系”不是流动的,而是僵化的实体,将女性固定在从属地位,所以才有了影片中姐弟不同生活间的张力。
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而活”的挑战
贝克将女性在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概括为从“为他人而活”到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转变对应于电影中安然和姑妈的不同选择,“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一点”二字精妙地传递出了女性改变之艰之难。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变化为何如此不易?
这与伴随女性主体意识萌芽的主体性撕裂有关。影片中,姑妈虽然被迫一次次做出退让,但她能够逆来顺受,自我消化;而当安然想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时,却面临着他人的阻挠,在物质支持和心理建构方面都遭遇困境。父权思维拖拽住女性前进的步伐,导致了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的犹疑与徘徊。
此外,这还与他我界限重构的现实有关。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自我主张与社会团结的平衡。但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被规训了太多太久的女性而言十分艰巨。影片的开放式结尾表明,在自我和他人的跷跷板上,安然没有最优解。因为在个体化时代,女性的义务究竟是自觉、自愿与自主,还是父权制规训下的阴影,往往难以判断。安然的故事道出了女性在个体化实践中所遭遇的阵痛。
在由性别、伦理和辈分所建构的家庭秩序中,姐姐是母亲的预备和后援,她一方面是家庭维系所依赖的成员,一方面也蕴藏着分裂家庭的可能——通过出嫁和独立的方式。针对出嫁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发展出了女儿是“外人”的文化观点;针对独立带来的对家庭团结的破坏,如同安然的遭际那样,则形成了定义其反社会化的指摘。在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中,女性的经历犹如走钢丝一般,摇摆的她们更需要社会性的支持。
作为女性视角的作品,《我的姐姐》不同于市场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后者中,女主人公往往只是迎合了女性对倒转性别刻板印象的简单而粗暴的渴望,沉迷于成为霸权男性气质的代言人,或满足父权制的期待,与其说世界围绕着她转,不如说她始终围绕着别人转。这样的作品无疑失却了反思的品格。
相比于现实事例,电影结尾处理得柔和了许多,就此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有锋芒的作品,而不是隔靴搔痒、大而无当的快销品。性别多元话语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热衷于再造“圣母”,却打着女性解放的旗号行消费女性之实的作品只会蚕食掉进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姐姐》的女性视角和现实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从年初的“李焕英”到“安然”,在聚焦女性的电影叙事中,看到的是女性一以贯之的美好品质,更有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也看到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而活”依然缺少结构性保障的困境……这些女性视角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反身性思考,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