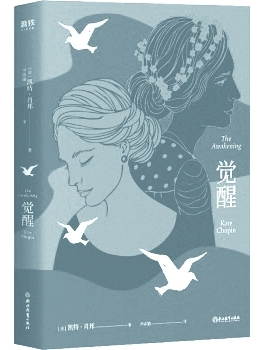■ 韩栋
“他的小说令我惊叹。小说中有生活,而不是编造;这种叙事艺术的关键在于,他用令人着迷的暧昧、不可思议的方式处理那些情节、老套的技巧和机关。他逃脱了传统和权威,进入自身,用自己的眼睛向外观察,以一种简洁直率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看到的东西。”这段话是凯特·肖邦对“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评论,几乎可以用于她自己。
初读凯特·肖邦的《觉醒》(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时,读者会收获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但看完一些故事的结局后,又会让人忍不住再次翻看前面的情节。而其中,《阿森奈伊斯》于我印象最深。
《阿森奈伊斯》的女主人公阿森奈伊斯由于丈夫卡佐的温柔求婚迷迷糊糊结了婚,婚后却觉得一切都不如意。“我受不了跟个大男人一起生活,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由着他把大衣和裤子挂在我房里,还当着我的面用我的浴盆洗他那双难看的脚丫子。”于是在哥哥的怂恿下,她逃离了家庭。一个月后,阿森奈伊斯发觉自己怀了孩子。回忆起丈夫的柔情,她迫不及待地回了家。
第一遍读时,我并不理解阿森奈伊斯这一做法。再看的时候,我不禁联想到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生之欲》的主人公渡边是一名公务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生命力逐渐干涸。然后他开始逃离当下生活,经过购物消费、依赖他人获得生活意义等各种尝试后,渡边察觉到了最初生活的意义,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渡边从一天天上班消耗活力,转变为做自己能做的事,完成了自我觉醒的转变,生命力开始绽放。这也正是《阿森奈伊斯》的妙趣!阿森奈伊斯最后燃起对丈夫的爱,基于自己的选择回到丈夫身边,正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最后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象征了阿森奈伊斯自我意识的新生。
自我选择与觉醒生命活力息息相关。当带着这句话审视整本《觉醒》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活力如何被激活、如何被损耗、如何被磨灭。《一双长丝袜》带来许多回味,含辛茹苦的母亲机缘巧合下尽情消费,其中确实有自我意识觉醒的萌芽,但与滋养生命的活力还有距离;《德蕾茜的孩子》中,社会地位、家族荣誉给自由爱情带来了让人心碎的毁灭;《分歧所在》则从男性视角出发,对男女的嫉妒之心有着截然不同的印象;从《阿卡迪亚舞会上》中女性的主动追求,到《暴风雨》中的生活形式与内心渴望之间,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一位正派女性》《一小时故事》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么多篇压抑的故事后,最后一篇《查理》中性格豪放的查理小姐,想通过成为淑女逆天改命,俘获心仪的小伙,终于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毫无负担地开怀大笑。充满喜感的失败让她认清自己做回自己,完成了自我觉醒。
“她们宠爱孩子,崇拜丈夫,把抹杀自我当作神圣的殊荣,希望自己能长出慷慨无私的天使之翼。”《觉醒》中这句话让我毛骨悚然。看完整本书,我才意识到它不仅仅是对小说中当下场景的描写,更是给19世纪已婚妇女们的形象概括。
作者凯特·肖邦20岁结婚,每两三年就生下一个孩子,30岁时已育有五子一女。直到31岁时丈夫去世,她才从生育孩子的重压中得到片刻喘息,而后开始写作。19世纪的女性收入来源非常有限,婚姻几乎是唯一的收入保障,正如《傲慢与偏紧》中的大龄剩女夏绿蒂认为“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的出路”。19世纪的欧美社会生活对女性并不友好,女性经济独立几乎不可能。那时的凯特·肖邦呼吁让这个世界更加宽容,让女性有机会通过尝试不同的生活,通过试错,有更多机会完成自我意识觉醒。我们把“女性”换成“人”,把“19世纪”换成“当下”,又何尝不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