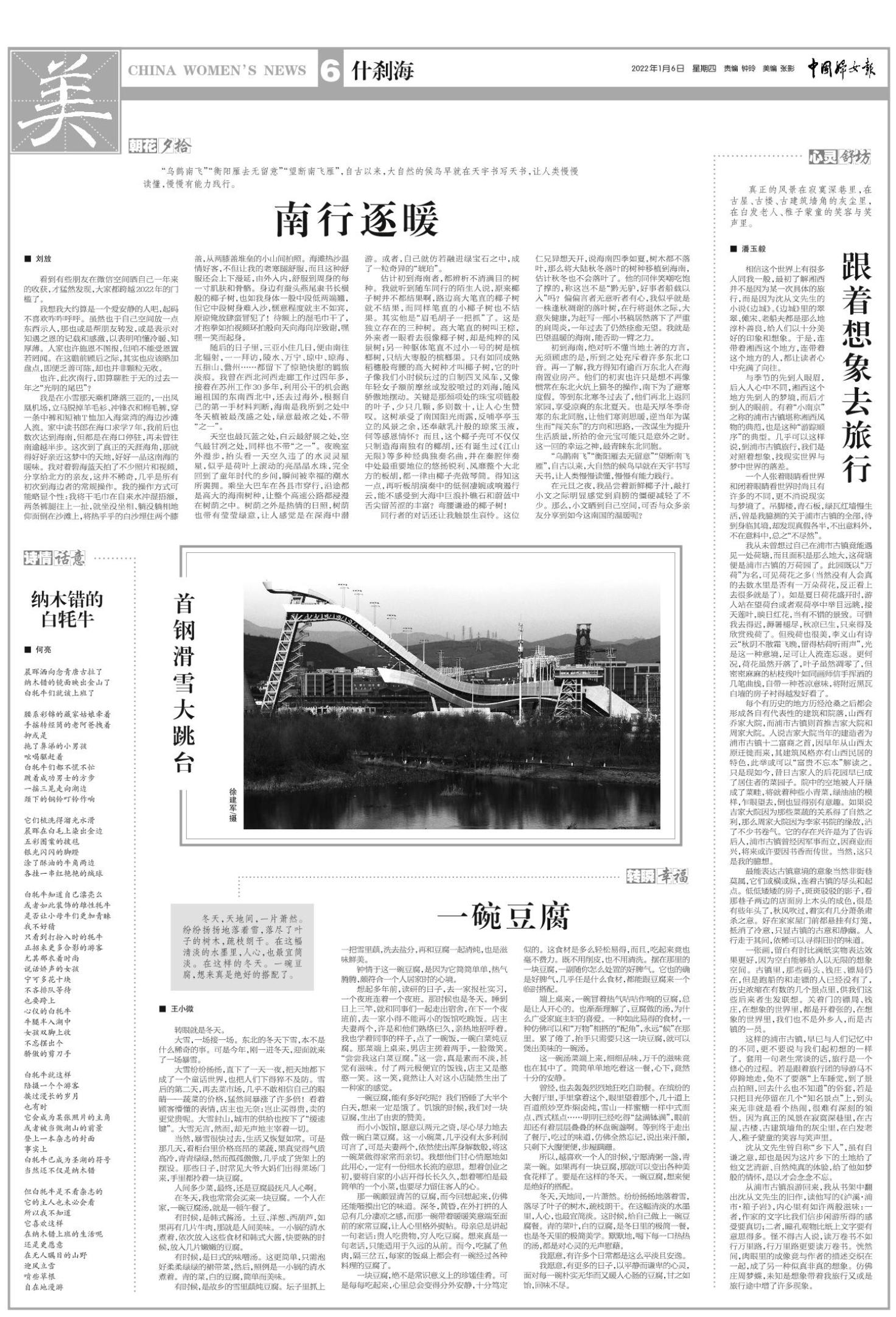真正的风景在寂寞深巷里,在古屋、古楼、古建筑墙角的灰尘里,在白发老人、稚子蒙童的笑容与笑声里。
■ 潘玉毅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同我一般,最初了解湘西并不是因为某一次具体的旅行,而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边城》里的翠翠、傩宋、老船夫都是那么地淳朴善良,给人们以十分美好的印象和想象。于是,连带着湘西这个地方,连带着这个地方的人,都让读者心中充满了向往。
与季节的先到人眼眉,后入人心中不同,湘西这个地方先到人的梦境,而后才到人的眼前。有着“小南京”之称的浦市古镇堪称湘西风物的典范,也是这种“游踪顺序”的典型。几乎可以这样说,到浦市古镇旅行,我们是对照着想象,找现实世界与梦中世界的落差。
一个人张着眼睛看世界和闭着眼睛看世界时尚且有许多的不同,更不消说现实与梦境了。吊脚楼,青石板,绿瓦红墙慢生活,曾是我臆测的关于浦市古镇的全部,待到身临其境,却发现真假各半,不出意料外,不在意料中,总之“不尽然”。
我从未曾想过自己在浦市古镇竟能遇见一处荷塘,而且面积是那么地大,这荷塘便是浦市古镇的万荷园了。此园既以“万荷”为名,可见荷花之多(当然没有人会真的去数水里是否有一万朵荷花,反正看上去很多就是了)。如是夏日荷花盛开时,游人站在望荷台或者观荷亭中举目远眺,接天莲叶,映日红花,当有不错的景致。可惜我去得迟,溽暑褪尽,秋凉已生,只来得及欣赏残荷了。但残荷也很美,李义山有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光是这一种意境,足可让人流连忘返。更何况,荷花虽然开落了,叶子虽然凋零了,但密密麻麻的枯枝残叶如同画师信手挥洒的几笔曲线,自带一种苍凉意味,将附近黑瓦白墙的房子衬得越发好看了。
每个有历史的地方历经沧桑之后都会形成各自有代表性的建筑和院落,山西有乔家大院,而浦市古镇则首推吉家大院和周家大院。人说吉家大院当年的建造者为浦市古镇十二富商之首,因早年从山西太原迁徙而来,其建筑风格亦有山西民居的特色,此举或可以“富贵不忘本”解读之。只是现如今,昔日吉家人的后花园早已成了居住者的菜园子。院中的空地被人开垦成了菜畦,将就着种些小青菜,绿油油的模样,乍眼望去,倒也显得别有意趣。如果说吉家大院因为那些菜蔬的关系得了自然之利,那么周家大院因为李家书院的缘故,沾了不少书卷气。它的存在兴许是为了告诉后人,浦市古镇曾经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将来或许要因书香而传世。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
最能表达古镇意境的意象当然非街巷莫属,它们或横或纵,连着古镇的尽头和起点。低低矮矮的房子,斑斑驳驳的影子,看那巷子两边的店面房上木头的成色,很是有些年头了,秋风吹过,着实有几分萧条肃杀之意。好在家家屋门前都悬挂有灯笼,抵消了冷意,只显古镇的古意和静幽。人行走于其间,依稀可以寻得旧时的味道。
一张画,留白有时比满纸实物表达效果更好,因为空白能够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古镇里,那些码头、钱庄、镖局仍在,但是跑船的和走镖的人已经没有了,历史浓缩在有数的几个景点里,供我们这些后来者生发联想。关着门的镖局、钱庄,在想象的世界里,都是开着张的,在想象的世界里,我们也不是外乡人,而是古镇的一员。
这样的浦市古镇,早已与人们记忆中的不同,更不要说与我们起初想的一样了。套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旅行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若是跟着旅行团的导游马不停蹄地走,免不了要落“上车睡觉,到了景点拍照,回去什么也不知道”的俗套,若是只把目光停留在几个“知名景点”上,到头来无非就是看个热闹,很难有深刻的领悟。因为真正的风景在寂寞深巷里,在古屋、古楼、古建筑墙角的灰尘里,在白发老人、稚子蒙童的笑容与笑声里。
沈从文先生曾自称“乡下人”,虽有自谦之意,却也是因为这片乡下的土地给了他文艺清新、自然纯真的体验,给了他如梦般的情怀,是以才会念念不忘。
从浦市古镇浪游回来,我从书架中翻出沈从文先生的旧作,读他写的《泸溪·浦市·箱子岩》,内心里有如许两般滋味:一者,作家的文字比我们信步闲游所得的感受要真切;二者,瞳孔观物比纸上文字要有意思得多。怪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更要读万卷书。恍然间,肉眼里的成像竟与作者的描述交织在一起,成了另一种似真非真的想象。仿佛庄周梦蝶,未知是想象带着我旅行又或是旅行途中增了许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