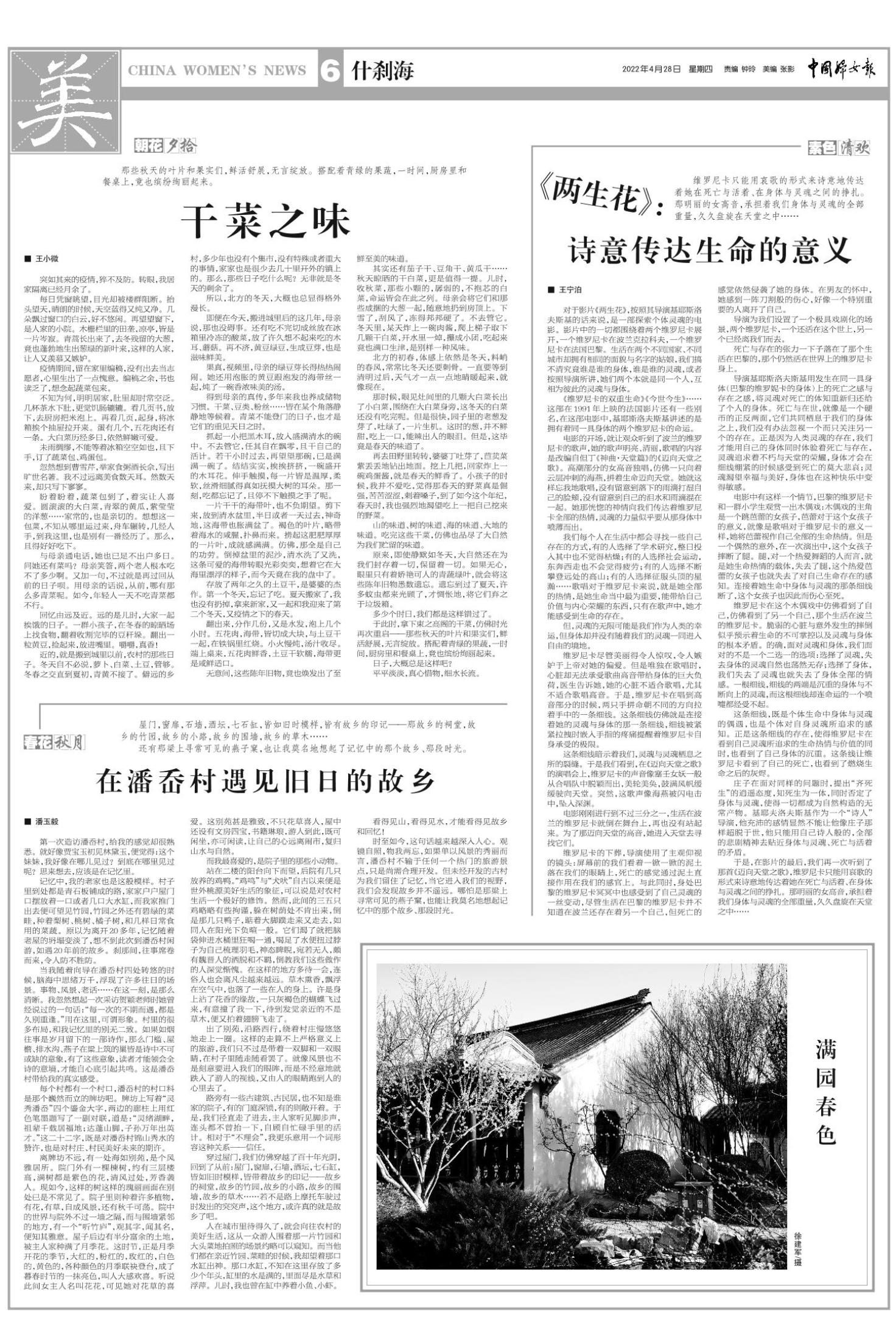维罗尼卡只能用哀歌的形式来诗意地传达着她在死亡与活着、在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挣扎。那明丽的女高音,承担着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全部重量,久久盘旋在天堂之中……
■ 王宁泊
对于影片《两生花》,按照其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是一部探索个体灵魂的电影。影片中的一切都围绕着两个维罗尼卡展开,一个维罗尼卡在波兰克拉科夫,一个维罗尼卡在法国巴黎。生活在两个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却拥有相同的面貌与名字的姑娘,我们搞不清究竟谁是谁的身体,谁是谁的灵魂,或者按照导演所讲,她们两个本就是同一个人,互相为彼此的灵魂与身体。
《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今世今生》……这部在1991年上映的法国影片还有一些别名,在这部电影中,基耶斯洛夫斯基讲述的是拥有着同一具身体的两个维罗尼卡的命运。
电影的开场,就让观众听到了波兰的维罗尼卡的歌声,她的歌声明亮、清丽,歌唱的内容是改编自但丁《神曲·天堂篇》的《迈向天堂之歌》。高潮部分的女高音独唱,仿佛一只向着云层冲刺的海燕,拼着生命迈向天堂。她就这样忘我地歌唱,没有留意到落下的雨滴打湿自己的脸颊,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泪水和雨滴混在一起。她那恍惚的神情向我们传达着维罗尼卡全部的热情,灵魂的力量似乎要从那身体中喷薄而出。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寻找一些自己存在的方式,有的人选择了学术研究,整日投入其中也不觉得枯燥;有的人选择社会运动,东奔西走也不会觉得疲劳;有的人选择不断攀登远处的高山;有的人选择征服头顶的星瀚……歌唱对于维罗尼卡来说,就是她全部的热情,是她生命当中最为重要,能带给自己价值与内心荣耀的东西,只有在歌声中,她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但,灵魂的无限可能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幸运,但身体却并没有随着我们的灵魂一同进入自由的境地。
维罗尼卡尽管美丽得令人惊叹,令人嫉妒于上帝对她的偏爱。但是唯独在歌唱时,心脏却无法承受歌曲高音带给身体的巨大负荷,医生告诉她,她的心脏不适合歌唱,尤其不适合歌唱高音。于是,维罗尼卡在唱到高音部分的时候,两只手拼命朝不同的方向拉着手中的一条细线。这条细线仿佛就是连接着她的灵魂与身体的那一条细线,细线被紧紧拉拽时嵌入手指的疼痛提醒着维罗尼卡自身承受的极限。
这条细线暗示着我们,灵魂与灵魂栖息之所的裂缝。于是我们看到,在《迈向天堂之歌》的演唱会上,维罗尼卡的声音像塞壬女妖一般从合唱队中脱颖而出,美轮美奂,鼓满风帆缓缓驶向天堂。突然,这歌声像海燕被闪电击中,坠入深渊。
电影刚刚进行到不过三分之一,生活在波兰的维罗尼卡就倒在舞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为了那迈向天堂的高音,她进入天堂去寻找它们。
维罗尼卡的下葬,导演使用了主观仰视的镜头:屏幕前的我们看着一锨一锨的泥土落在我们的眼睛上,死亡的感觉通过泥土直接作用在我们的感官上。与此同时,身处巴黎的维罗尼卡冥冥中也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一丝变动,尽管生活在巴黎的维罗尼卡并不知道在波兰还存在着另一个自己,但死亡的感觉依然侵袭了她的身体。在男友的怀中,她感到一阵刀割般的伤心,好像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离开了自己。
导演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极具戏剧化的场景,两个维罗尼卡,一个还活在这个世上,另一个已经离我们而去。
死亡与存在的张力一下子落在了那个生活在巴黎的,那个仍然活在世界上的维罗尼卡身上。
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发生在同一具身体(巴黎的维罗妮卡的身体)上的死亡之感与存在之感,将灵魂对死亡的体知重新归还给了个人的身体。死亡与在世,就像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共同栖息于我们的身体之上,我们没有办法忽视一个而只关注另一个的存在。正是因为人类灵魂的存在,我们才能用自己的身体同时体验着死亡与存在,灵魂追求着不朽与天堂的荣耀,身体才会在细线绷紧的时候感受到死亡的莫大悲哀;灵魂渴望幸福与美好,身体也在这种快乐中变得敏感。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巴黎的维罗尼卡和一群小学生观赏一出木偶戏:木偶戏的主角是一个跳芭蕾的女孩子,芭蕾对于这个女孩子的意义,就像是歌唱对于维罗尼卡的意义一样,她将芭蕾视作自己全部的生命热情。但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在一次演出中,这个女孩子摔断了腿。腿,对一个热爱舞蹈的人而言,就是她生命热情的载体,失去了腿,这个热爱芭蕾的女孩子也就失去了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感知。连接着她生命中身体与灵魂的那条细线断了,这个女孩子也因此而伤心至死。
维罗尼卡在这个木偶戏中仿佛看到了自己,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那个生活在波兰的维罗尼卡。脆弱的心脏与意外发生的摔倒似乎预示着生命的不可掌控以及灵魂与身体的根本矛盾。的确,面对灵魂和身体,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选择了灵魂,失去身体的灵魂自然也荡然无存;选择了身体,我们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身体全部的情感。一根细线,细线的两端是沉重的身体与不断向上的灵魂,而这根细线却连命运的一个喷嚏都经受不起。
这条细线,既是个体生命中身体与灵魂的偶遇,也是个体对自身灵魂所追求的感知。正是这条细线的存在,使得维罗尼卡在看到自己灵魂所追求的生命热情与价值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身体的沉重。这条线让维罗尼卡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也看到了燃烧生命之后的灰烬。
庄子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提出“齐死生”的逍遥态度,知死生为一体,同时否定了身体与灵魂,使得一切都成为自然构造的无常产物。基耶夫洛夫斯基作为一个“诗人”导演,他充沛的感情显然不能让他像庄子那样超脱于世,他只能用自己诗人般的,全部的悲剧精神去贴近身体与灵魂、死亡与活着的矛盾。
于是,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那首《迈向天堂之歌》,维罗尼卡只能用哀歌的形式来诗意地传达着她在死亡与活着、在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挣扎。那明丽的女高音,承担着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全部重量,久久盘旋在天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