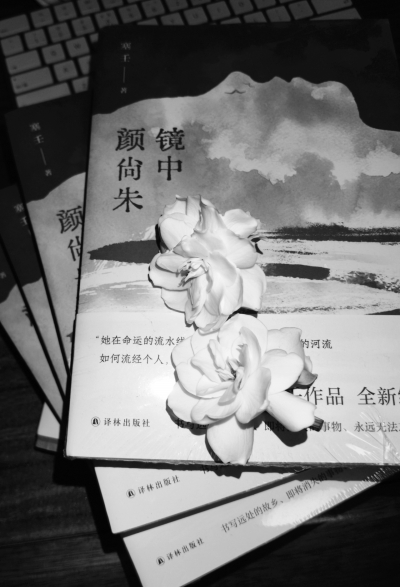■ 口述:塞壬 作家 ■ 记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人物简介·
塞壬,原名黄红艳,1974年出生于湖北,现居东莞长安。2004年下半年开始散文写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天涯》《花城》等刊;已出版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沉默、坚硬,还有悲伤》《镜中颜尚朱》等;作品曾两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等。
写作,并不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在写作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以及自己与世界的联系。
在与孤独的博弈中奔向更好的自己
3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走上写作之路,要从20多年前的我在广州的流浪生活说起。
2000年,我辞掉了在老家的记者工作,原因是因为同工不同酬。我只身一人来到了广东东莞市,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在一家工厂里做工,体会着人世间的辛酸苦辣。在那些落魄、疲惫的疾走岁月,我身边似乎没有值得信赖的人,没有可以倾诉的灵魂。形影相吊的岁月里,我把自己所经历的状态、担任的工作、遇到的事、碰到的人,写进了我的第一本书《下落不明的生活》。我在书中记录了身处人生低谷的自己,也写下了保持内心的鲜活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
于是,我把自己的名字黄红艳改为塞壬。那个关于塞壬的传说,让人充满了遐想。或许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传说、一个传奇。我希望我写出的作品也有传说故事中里那种魔力。
2009年,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正式成为东莞市长安镇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如果没有漂泊的生活,也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之路。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那段时光,带给我内心对现实不服输的冲劲。
记得我在一个鞋厂工作的时候,鞋厂每周都要交一份手写的工作小结,写这种小结的文字可以非常纯净,它的指向明确,清澈透明。我当时写的时候就很放松,或者说,进入这样一个鞋厂工作,就是能养活自己,并没有多余的想法。一个多月之后,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找到我,说我的文笔可以协助办企业的内刊,说她已通知人事主管,把我调进行政部。我的天哪,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吧,“是金子总会发光!”
历数我的人生过往,是文字让我发光,让我有了不同的人生。后来到企业做宣传、做广告杂志经理人等,文字就不知不觉地和我的生活形影不离了。我对文字的信赖,就像每个人相信雨后会有彩虹一样,渐渐地,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生存状态也和从前不同了。我当初写散文,根本没有想到荣誉、功利以及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只想在写作中摆脱困境,在无边无际的孤独中警醒,奔向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曾在《奔跑者》中写道:“奔跑,它是那种关于精神、意志、飞翔、梦境、痛苦、迷茫、内省以及完成灵魂自我修复的放逐。它是慢慢积累的生命之重,它包括灵魂的钙质与铁性,它加重了血液之盐。奔跑,在与孤独的博弈中,我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的突围,自我警醒、激励,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
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感觉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工业重镇黄石,尽管我在广东东莞生活多年,但对于故乡的记忆从未消失,故乡的风物、器具还有人,时常像水墨画一样在我脑海中漾开,然后滋养着我的每一个疲惫的夜晚,让我在甜甜的回忆中入睡。
我的笔触走过对故乡的记忆时,情感都是较为复杂的,遗憾、悲悯,还有坚硬。
在《消失》这篇散文里,我曾表达对故乡的记忆和年少成长的朦胧之痛。随着岁月的逐渐拉长,有些东西渐渐地在消失,有些东西渐渐地在萌生,对于故乡那片茂盛的水稻田,和那生活居住的钢铁城,我的记忆一直是那么清晰。我在文字中,一遍遍感受逝去青春的岁月,寻找那份伤感又美好的回忆,越来越体会到文学是可以在情感上臻至一种自我陶醉,如果硬要说对抗,那一定是文学表达让它在那里对抗,达到表达的效果。
回想自己出生的那个叫西塞的地方,有一种叫悲迓的语言,是楚剧唱腔的一种,主要表达人物内心悲伤凄凉的情感。悲迓以自己独特的方言流传千年的习俗与审美,我在《悲迓》那篇文章里承载了作为一名远在他乡的游子的自己充满血性的情感。尽管我无法还原地方文献资料那样的宏愿,也无法完成悲迓最初的模样,但是我能做的是在无数遍的回忆中,寻找到悲迓直到远去,它在我心里是永恒的存在。
存在即为真实。这些年来,对于散文的创作,我觉得真诚和真实是散文的全部,散文不只是以情动人,还有一种表达“我”的文本,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感觉。
当然,这种表达“我”,在我的散文中的“我”,应该是一个泛“我”,它书写的“我”可以是他者的经验,以我的视角来推进。在我看来,散文有浩瀚的容量,它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细水深流。对散文容量的拓展,是一个散文作家探索散文写作难度的重要指标。
向下向内式书写生活真善美
我一直认为,写作不仅需要投入自己的情感,还需要一个作家的自我更新能力、续航能力以及丰富的经验储备。
面对每一个文字、每一次创作,我都是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
两年前,我就曾经掩藏自己的作家身份,应聘到东莞的一个电子厂,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后来因担心交社保而泄漏身份,便辞职了,我把这一个月的亲身经历,写成一篇散文《无尘车间》。那篇文章发表于《天涯》杂志后,有作家朋友、读者纷纷来电、来信,说我把这种卧底的经历变成了文字,仿佛每一个字符都有了一种灵动。
后来我写《日结工》的时候,陆续到许多工厂进行体验,比如五金厂、狗链厂、鞋厂、玩具厂、印刷厂等十多个厂,坚持体验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半年里,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一天,新的人、新的事物、新的环境,能让我写下对生活的新理解。
《无尘车间》《日结工》这两篇文章都将收入《无尘车间》这本书,该书在今年正式出版后,将是我作为东莞作家推出的第一部打工文学作品。和过去绝大多数打工文学不同的是,我并不完全把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上,而是更多地关注自我,我进入这个群体中的反馈和一种全新的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重新认识了自己。
创作来源于生活,只有不断参与到现实生活,向下、向内式的书写更能反映生活的真善美,才能写出接地气的作品。这就是虚构与散文的重要区别,也就是说,我是以散文的手法写了《无尘车间》和《日结工》。它是向内的、关注自我的,关注的是个体进入陌生世界的反应,它将重新激活作品的人格与人性。
2022年出版的《镜中颜尚朱》一书里,在《即使雪落满舱》《追赶出租车的女人》《缓缓的归途》《隐匿的时光》《翁源手记》等文章都能感受到浓烈的情感,在它宏阔的外部现实世界里,还有一种抵达内心的精神高度,这也许就是读者与作者灵魂相似的部分。
对于未来,我依然充满太多的向往,我一直在尝试着探索小说与散文的边界,试图找到两种文学形式过渡的交点。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并且我很迷恋这种虚构,对于我来说,它充满着深深的魔力。
未来的写作,我将会把写小说与写散文并重,在虚构与非虚构中实现一种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