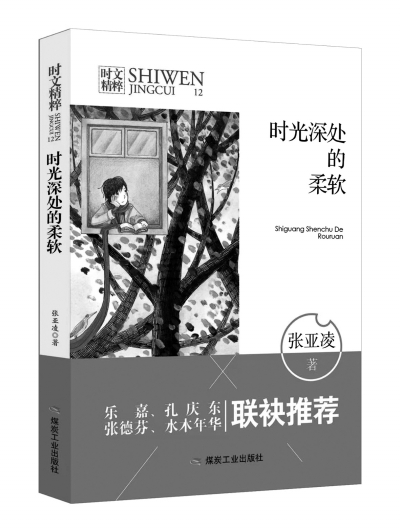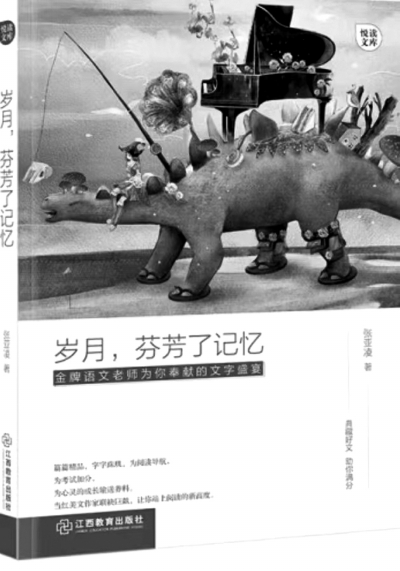■ 口述:张亚凌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亚凌老师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
她说:“像老师这样学会将幸运赋予自己,你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幸运、幸福!”
“52年前,我不到周岁,巷子里有三个孩子出天花,两个都因医治无效而离开这个刚刚落脚、尚未开始就已结束的人生,只有我命大,只是多天高烧不退,烧坏了右眼。我能活着本是劫后余生,得有多大的幸运,又得有多深厚的感激……我是幸运的,看了这么些年的天高日头红,疾病落下的右眼失明又何妨,不活好自己,连老天都对不起。”
张亚凌语音刚落,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站起来,纷纷为自己贴上幸运的标签。
有的孩子是流着泪讲述的,泪花中的笑可不可以理解为释然?有的孩子讲述时颇为轻松,轻松可不可以理解为破茧而出?有的孩子欲言又止最终说出,说出后会不会改变了认识?有的孩子是被别的孩子硬推上讲台,他会不会因此感受到友爱?有的孩子讲述别人的事,语言里满是疼惜,被关注者那一刻会不会被暖意包裹?更多的孩子是踊跃站起,鼓足勇气说出,说出的会不会是久积心头的疼?
眼前情形让张亚凌很是欣慰:她看见了孩子们对过往的放下、释然、超越,她更看见了不屈、挑战、感恩……
张亚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以自己为标本,以生命为课堂,努力激活哪怕最自卑的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只有经历过黑暗的人,才会竭力帮助他人寻找光源。
以下是张亚凌的讲述:
走出自卑的泥淖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平凡”一词的解释很简单,“平常,不稀奇”。而我,想触摸“平凡”二字,都觉得奢侈。
平凡的人就是沙漠中的一粒沙,沧海中的一滴水,与99%的人无异。对,“无异”。说到这里我才觉得能够“无异”也是莫大的幸福——我“有异”。
肤色黑,没事,多年后我发现有比我更黑的,我只是白得不明显,刚好还遮盖了一脸雀斑;个子矮,不怕,似乎打篮球才要求个子高,那项运动我不喜欢,做衣服时还省布料;一紧张说话就结巴,不打紧,踏实做最重要,将说的时间留给做,或许会做得更好,还避免了祸从口出。说句实话,在我眼里还真没让人绝望的缺陷。
或许就是因为我太皮实了,能接纳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感动了老天爷,他萌生了历练我、磨砺我的念头,硬生生地将我与普通人彻底划分开来——幼时一场疾病导致右眼失明。因了老天爷的这个记号,我想混入“平凡”变得难如登天。
儿时很少有朋友,我学会了以日记的形式跟自己聊天,作文倒写得越来越好,每次都被当范文读,给了我些许的骄傲。
只是——
初二换了语文老师,新语文老师很是奇怪,每次讲评作文都会先说一句“这次作文写得好的有某某、某某等”,而后将点到名的学生的作文当范文读,最后总说一句,“时间有限,其他的就不读了”。我从来没被点名表扬过,作文自然也没被读过。
那一年每次上作文课,对我都是一场折磨,恨不得将头深深地埋进课桌里。而握起笔,又告诉自己要认认真真写出最好的作文。表扬不表扬是老师的事,写好才是我能做到的事。
也记得是次年3月,全县举办了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我是全县唯一的一等奖,也是我们学校唯一获奖的。颁奖回来,学校又召开了一次师生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读自己的获奖作文。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哽咽了。下面的掌声响了起来,他们一定认为我是声情并茂。那一刻,我终于将自己从被忽视的泥淖中拔了出来。
那次以后,我坚定了做好自己不在乎任何人的评价,包括老师。我也明白了,一个人只有悦纳自己,才不会敷衍自己、怠慢自己,从而辜负了自己,才会想着以更好的方式去寻找去靠近那个更为美好的自己,才会督促每一天的自己都要在努力中得到锻炼与成长。
悦纳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打磨自己。
老天爷让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模样或性情来到这个世界,肯定有自己的理由,不用自卑,只需想想怎样才能更好。
那篇作文是颗种子,叫“文学”
对文学最初的痴迷源于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订阅的《少年月刊》。每每拿到新杂志看着上面的文字,心就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各种小念头小想法不再矜持,你推我搡你拥我挤,身手敏捷的干脆直接迸溅起老高:
原来没必要老想着用文绉绉的词语,咋样说就咋样写也不错;
原来既可以实实在在地写真人真事,还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
原来这种见不得人的小心机,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写在纸上还不怕别人笑话;
原来因为想偷懒而跟妈妈犟嘴这种丑事,也可以写得这么轰轰烈烈吸引人……
那么多“原来”让我自个悟出了门道:写作文不全是自己漂漂亮亮,做的事风风光光,就是给别人说说眼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当我将自己悟出的说给母亲时,她惊喜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凌儿就是聪明。”被母亲一表扬,我立刻就不知道自个几斤几两了,哪里只是“胸有成竹”,竹子叶都长到嗓子眼啦,当即拍着胸脯给她保证:将来我写的也要印在书上!
于是我开始天天写日记,只为了那个保证。
初二时我发表了一篇作文,逢人就嘚瑟,指来点去的,手指几乎把“张亚凌”三个字指认模糊了。那篇作文应该是颗种子,叫“文学”,它摇着晃着让我开始做梦——成为作家。
大学后,文章发表多了,心境倒平静而开阔。
大学时阅览室是我的主阵地,图书馆是我的能量库,里面文史哲的书几乎逐一借阅,以至于离开大学30年后的今天,在阅读方面没有丝毫饥饿感。
在我,“整个大学=阅览室+图书馆”。多年后受邀回母校给文学院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写作,回忆起大学校园里的自己,我说了一句话:“多阅读多写作,这是文学院学生的底气。”
在互相陪伴与成就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为语文老师,我深知要让孩子们写好作文,不是拿着作文指导书照本宣科就能水到渠成的,而是老师要以身示范写好“下水作文”就可以立竿见影。
我选择了以“师生同题写作”来陪伴孩子们。
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却不能仅仅落在遥不可及的偶像身上。我喜欢怎样的自己?那个“自己”是不是与此刻的我中间还隔着一段距离?那个“自己”是不是让我一想起就心情澎湃就想铆足劲儿前行?那个“自己”啊,就像块光斑,吸引着我全力奔跑。于是我写了篇《我喜欢的自己》:
“我喜欢带着孩子们奔跑的自己。”
“我害怕自己不慎落入‘不阅读不写作的老师却在教一群孩子读书与写作’的魔咒,一直满怀激情地大量涉猎各种知识,并在写作中乐此不疲。我读书或写作,以身示范,让孩子们感受到文字的芬芳文学的美好,他们在阅读中酣畅地呼吸在写作中自由地奔跑。看着他们对美渴望,对好向往,朝着美好全力飞奔,我满心欢喜。”
“我以飞奔的姿势引领着孩子们,他们跑起来就是最美的风景,我怎能不喜欢那一刻的自己?那一刻的自己,应该是因为拼搏被孩子们深深地喜欢,更被我自己所喜欢。”
在我分享后,涌现出好些触动人心的佳作,程凯茹是这样写的:
“我喜欢朝着目标,努力奋斗的自己。‘走在前面的人,总会被后面的人仰望。’这是我步入初中时送给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要成为更优秀的人,想要被别人仰望,甚至想成为中国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我要为自己的青春着上最美的颜色。”
“为了成为那样的人,我下定决心,制定目标,努力奋斗,急速奔跑。晚上定好了闹钟,心心念念着自己明天的学习任务是否圆满完成。现在叫醒我的不是妈妈的唠叨,而是内心的恐慌和心里的责任。美好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在自己清晰响亮的读书声中,我找到了飞翔的感觉;在笔‘唰唰’划过的声音中,寻见了更美的自己。”
“乐观向上,我提升了自己,我满怀激情地走向心怀目标努力奋斗的那个自己。”
前行中最好的陪伴是让我们看到方向,为我们照亮脚下的路,慰藉又温暖;成长中最好的同行是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纠正着我们的言行,向上而明媚。那些美好的陪伴与同行,宛如茫茫大海上或沉沉暗夜中的灯塔,让我们的人生不偏离航向。如此想着,我写下了《你是我的灯塔》:
“有没有一个人,燥热时给你清凉,迷茫时为你拨开云雾,灰暗时为你而点亮?我很幸运,就拥有如灯塔般的一个人——苏轼。”
“年轻,充沛的精力让吐出的每句话都显得志在必得。不知深浅便狂妄自大到好像整个世界就是自己手底的一盘小棋,似乎只需轻轻划拉一下,就能够随心所欲拥有一切,还颇有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味儿。那时最喜欢故作深沉,常挂在唇边的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好像年轻的目光已看穿尘世,自己已所向披靡。”
“苏轼的诗文拿来就用,踏实又过瘾,恰如年轻人对付这个世界的强大武器。”
孩子们开始寻找自己的灯塔,赵婉晨的灯塔就是她的母亲,点滴琐事里尽是爱的光芒:
“人生如同漂泊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有时暴风骤雨有时万里无云,自有起起落落。母亲,你就是我人生大海中的灯塔……”
看着教室外面的两棵树,桃树与白玉兰,我给孩子们这样描述:
“桃树具有少女情怀,所有的浪漫与心事,无遮无掩,一股脑儿都捧到了你的面前,一树繁花,满眼粉红,接纳不接纳,随你。玉兰则走了另一极端,沉静高贵地矜持着,内敛含蓄地伫立着。不试探,不靠近,远远地,只在静默里等待。‘等待’二字或许都是我的多情,它似乎已沉浸在独处的美好里了……”
在心思与语言一样细腻的赵翔宇笔下,看着桃树,她是这般描述:
“春风习习,带来一幕春光,送来一味春情。桃花的香是浓郁的,热情的。她不含蓄,也不懂女儿家的欲拒还迎,只一味地向你张开双臂,把最芬芳的美好毫无保留地给你。它是纯净的,阳光给了它亮,她便亮;给了她香,她便香。世界赐她桃之名,她便以乳白粉嫩的色彩示世……”
在他们有点疲惫时,我们一起写下《我是如此热爱生活》;在他们有点迷茫时,我们一起写出《我的未来这般清晰明媚》;感觉到班里有早恋倾向需要引导时,我们一起写了《年少的喜欢》;心疼孩子们熬夜苦读,我们一起写了《抱抱自己》……
书写在我,是对孩子们最温暖又最理性的陪伴。
不只是师生同题写作,课堂上,教学中,生活里,任何小感动小细节我都会记录下来跟孩子们分享,让孩子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写作很简单,接地气有思想就好。而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出现在各种报纸上杂志里,甚至被一些省市选为考试阅读题,孩子们心里,那是鼓鼓的能飞起来的骄傲啊。
突然想嘚瑟一下我的孩子们:赵欣悦的作文被《读者》转载过,在全国写作大赛中我的孩子们多次获得第一名的殊荣,他们已在各种报刊发表了3000多篇习作,有80多个孩子被各种报刊以“校园文学之星”推出……
哪里是我在成就孩子们,最好的陪伴是彼此成就。
当我成为一些杂志的签约作家,当我成为一些报刊的专栏作家,当我的文章被译为外文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当我的散文随笔大量进入考卷,当我被称为“中高考热点作家”时,我要感谢的,是曾有缘相遇的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为了以自己满意的方式陪伴他们,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