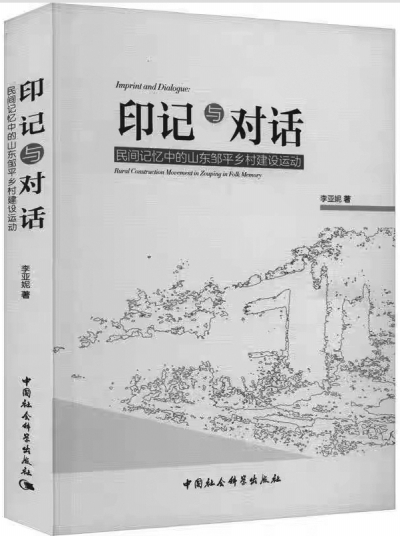阅读提示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梁漱溟却认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在这场运动中,女性在哪里?女性如何参与?近百年后,她们又是如何回忆这场运动的?《印记与对话:民间记忆中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既是对这场乡村社会改革的历史回望,又希冀能为当代乡村振兴的探索提供思考。
■ 李亚妮
20世纪3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发生在旧中国的土地上。在山东,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乡村建设体系。在乡建研究院的理论指导下,邹平成立了乡学村学组织,创办了《乡村建设》刊物,建立了农场试验区和经济合作社等组织。全国性的乡村建设理论研讨会在邹平召开,并成功举办过两届农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全县50%以上。可以说,到1935年邹平已经成为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也成了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典范。但是,同年作为领导者的梁漱溟却深刻意识到,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面临“两大难处”,即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也就是“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仍然提到“乡村不动”的问题,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些改良措施是不被农民欢迎和接受的。
为何这位从北大讲坛走向乡村的哲学家与实践者发出这样的拷问?性别研究是解答的视角之一。那么,在这场运动中,女性在哪里?女性是如何参与的?近百年后,她们又是如何回忆这场运动的?随着研究深入,我看到了更多的身影,也听到了更多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日前出版的这本《印记与对话:民间记忆中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文献中“消失”的她们
最初,我将研究定位在邹平,不仅仅是因为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名气,更多是因为这里丰富的文献资料,让我有研究的资料底气。自1931年至1937年,山东乡建研究院发行《乡村建设》刊物,共7卷,183期,翔实记录了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但是,在文献查阅中,我却发现有关“妇女”或“女性”的文献很少,梁漱溟先生也很少谈到妇女问题。两篇论及妇女或女性的文章,与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一致,他认为妇女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出现旧礼俗被破坏而新礼俗未建立起来的麻木状态。文献资料中涉及妇女的文章不多,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婚姻状况调查、家庭生活调查、教育统计、风俗调查与风俗改良等官方调查统计数据或活动中,而对于作为个体的女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以女性承担为主的织布活动和织品展览的统计中,也很少看到女性的身份,偶有出现也是以“张王氏”这样的名字,大多织品的出品人则是一位男性收集者,同时他也是展览会的获奖者之一。在其他的经济合作社中就更看不到女性的姓名。我们无法看到女性群体或个体对这场社会运动的感受、体验和想法。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女性群体是“消失”的她们。
田野中“找回”她们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历史课本或其他文献资料上了解这场短暂而又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去邹平之前,我也以为那都已是纸上的历史。但当我踏上邹平的土地,当我与97岁目不识丁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访谈时,老人家兴致勃勃、字正腔圆地说,“梁漱溟,为邹平办了好事,对老百姓不孬”,我才感受到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在陌生人进入村子调研已被高度警觉的时代,带有“梁漱溟”字眼的调研却被热情接纳,虽然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已大多不在世,但偶尔遇到的高龄亲历者仍然对这段历史有无限怀念,他们尽可能地搜寻记忆,从家中的储藏室中翻找历史图片,与我一起辨认或猜测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打听到某村有一位95岁高龄的老奶奶。我迫不及待又内心忐忑地来到村口,带着学者对资料获取的私心,希冀这位老奶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因为在寻求被访者的路上,我有太多的希望与失落。当我走进小院时,眼前是绿油油的小菜、金灿灿的玉米和整洁的院落,这位发白慈祥又利落的老人让我不禁泪湿。那个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我和老奶奶一边手剥玉米一边回忆那段历史。老奶奶讲述了自己的亲妹妹参加乡建研究院学堂时的情景。当年她12岁,妹妹10岁,她是家里的老大,要干家务照看更小的弟弟们。她却记得妹妹学的儿歌,如“大羊大、小羊小,上山上去吃青草”等。当这首80多年前在邹平乡农学堂里教授的儿歌从老人口中唱出的时候,我听到了她的兴奋和羡慕。她们当时又何尝不想参加呢?
一位88岁高龄的老奶奶,是我访谈的亲历者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她也是一位由缠足到放足的亲历者。1935年正是她缠足的年龄,在研究院的督查下,她的脚缠了又放了。她感叹自己是放足的受益者。
抢救式的调查让我在田野中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感动。92岁的老奶奶在我第二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讲述第一次访谈时没想起来的发生在自己七八十年前的经历,生怕刚刚捡到的宝贝再次丢失;98岁的老奶奶在养老院公寓里给我讲述自己当童养媳的经历;一位93岁的老奶奶讲述童年时期带着弟弟妹妹乞讨的生活;一位95岁的老奶奶讲述自己刚结婚时因为不会做针线活儿而回娘家求助时的闺女情;一位88岁的老奶奶会在我第二次访谈时说,“我想起来个放脚歌,我给你唱唱”,然后完整唱出五六岁学过的放足歌。不知道在我第一次访谈离开后,她想了多少次。
虽然由于方言的原因,我不能字字听懂,一些敏感的或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会被我的迟钝过滤掉。我苍白的语言无法展示她们生活的丰富,也无法抵达她们的内心。但在她们的讲述中,从她们的眼中,我读到了历史中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感受。
这本书中涉及的访谈对象有103位,年龄分布于20世纪邹平社会变迁的各个历史阶段,包括1930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其中有21位出生于1932年前,即在童年或少年时期以不同形式见证过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能清晰回忆的有6位女性。男女被访者在对地方知识的回忆和讲述中,有着不同的系统和语汇,对乡建的回忆和描述也是不确定的。女性更多回忆的是自己参与的具体劳动、放足运动、卫生医疗等与女性生育、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无人提到经济合作社的事情。
每个人的讲述都不是为了给我提供这段史料,而是在讲述她们自己的生命史和生活史。她们经历了乡村建设运动,也经历了农业集体化和改革开放,社会变迁在生命个体和家庭生命历程中都留下了印记。而我作为一个陌生的提问者,猛然闯入她们的生活,闯入她们的记忆,不知会给她们留下什么。我的私心促使我无休止地提问,但从未被拒绝。不管是在秋收的繁忙中,还是棚户区的杂乱中,即使是在疫情中的2021年,他们也都对我坦诚接待。我又何德何能,得此幸焉。我无法再现历史的真相,只能适当记录她们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