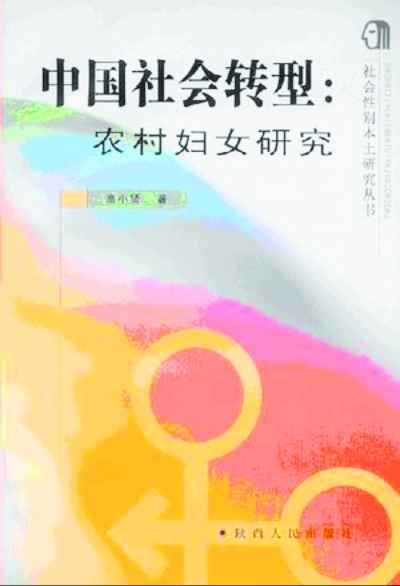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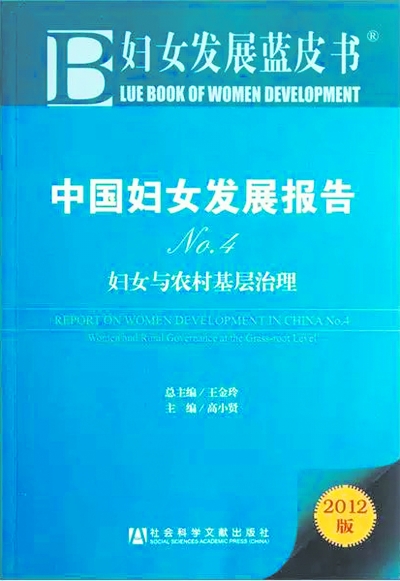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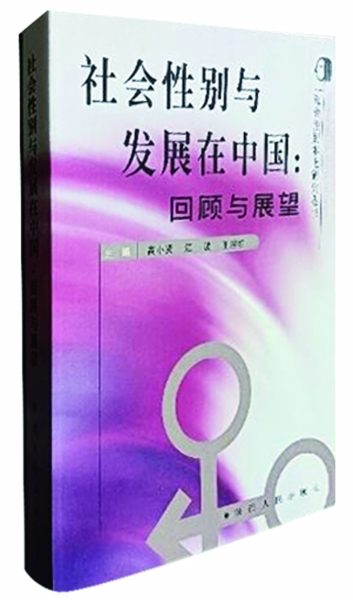
■ 陈聪
2025年4月2日,中国性别研究者高小贤逝世。这位20世纪80年代便扎根西部山区的学者,用数十年将社会性别理论锻造成开垦黄土地的犁铧。值此清明之际,重读其遗作《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等,不仅是对一位逝去思想者的追思,更是打捞被遮蔽的性别研究“前史”的呼唤。
理论的本土化突围:从田野裂缝中生长
1986年春,陕南丹凤县卫生院的一份孕产妇死亡记录,成为高小贤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档案纸上,“子痫”等字眼冰冷地排列,吸引了这位入职妇联四年的干部的注意。
而当西方女性主义者在书斋里解构“父权制”时,高小贤在关中平原的麦田里发现了更具体的现象。男性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催生出“农业女性化”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她在书中犀利地指出:“所谓‘男工女耕’的‘自然分工’,实则是将妇女禁锢在低价值生产领域……”
这种性别洞察力,在“彩礼异化”研究中达到顶峰。通过对比20世纪80年代与千禧年后关中农村的婚姻实践,高小贤揭示出市场经济对传统伦理的复杂重塑:当彩礼从“礼仪性象征”异化为“婚姻市场资本”,妇女反而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这种预警,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
行动研究的中国范式:让知识长出双脚
在陕南贫困山区,高小贤和她的同事们把“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在地化。面对文盲率高的农村妇女,她采用“泥土教学法”——用树枝在田间画出“性别分工树”,以玉米粒计量劳动时间分配。当妇女们发现自己在家庭经济贡献占比超60%却无决策权时,沉默的群体开始质问:“我们的价值去哪儿了?”
丹凤县孕产妇保健项目更展现其干预智慧。面对农村妇女羞于就医的困境,团队创造性将产检率与“五好家庭”评选挂钩,动员族长参与健康培训,三年内使孕产妇死亡率下降67%。更具意义的是项目的“裂变效应”:获得健康保障的妇女自发组建合作社,利用世行小额贷款发展庭院经济;识字班结业的妇女开始竞选村委,改写“女人不上台”的村规。高小贤在书中写道:“赋权不是恩赐,而是让妇女在改变生存境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改变历史的力量。”
而在紫阳县推行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中,陕西妇女研究会帮助农村妇女争取到40%的社区项目决策权。高小贤在此展现出其思想智慧:“性别平等的本质是权力重组,这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妇女的政治能力锻造。”
未完成的对话:80年代精神与当下突破
在电商进农村、短视频重塑乡土文化的今天,重审高小贤的忧思更具现实意义。她曾预警市场经济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异化:彩礼从“礼仪性象征”异化为“婚姻市场定价工具”,打工经济催生的“临时夫妻”冲击传统伦理,这些30年前的田野发现,与当下热议的性别议题形成共振。
书中对“本土化”的坚持尤显珍贵。在引入世界银行社会性别评估框架时,高小贤和研究团队创造性加入“上门女婿土地权”“丧偶妇女祭祖权”等本土指标。这种理论自觉,恰是对当下某些机械套用西方性别理论现象的警示——我们是否遗忘了关中农妇争夺玉米地灌溉权的抗争?
随着部分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前辈的离去,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紧迫的学术代际更迭。高小贤们留下的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条未尽的道路:在陕西妇女研究会发黄的会议记录里,在丹凤县妇女合作社的账本褶皱中,在那些由农村妇女亲手绘制的性别分工图谱上,依然跃动着思想解放的原始能量。
当性别议题引起网络热议时,或许我们需要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田野现场,重拾高小贤“把学术做进泥土里”的笨功夫。毕竟,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转型仍未完成,而每一次对历史的打捞,都是为了照亮前路的沟+壑。这位永远行走在乡土路上的学者,最终将自己的生命也化作了路标——指向更平等、更包容、更扎根大地的性别未来。
(作者为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