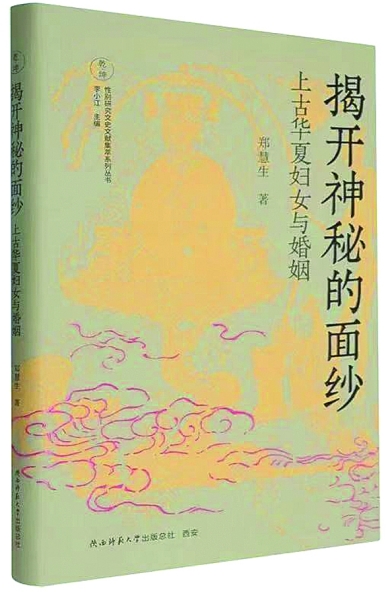
·阅读提示·
《揭开神秘的面纱: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以丰富的原始材料、独特的性别视角、结合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挑战了传统史学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叙事。该书最终指向一个根本命题:华夏文明的源头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性别权力结构。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但其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忽视妇女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不要忽视那些被正统叙事遮蔽的声音!文明的真相可能就藏在神话与史实、文字与器物的轻盈面纱之后。
■ 张年年
“乾坤”书系中的旧作新刊
日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策划的郑慧生教授的《揭开神秘的面纱: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一书正式再版,该书原属李小江老师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此次再版,被收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特色品牌——“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乾坤”书系)。
“乾坤”书系一方面甄选旧作,另一方面吸纳新作,以求继续推动已成气候的妇女和性别研究。郑慧生教授的大著在上古妇女与婚姻制度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此书虽已出版40年左右,属于“旧作”,但书中的许多论述思路开阔、视角新颖,其研究放在现在也颇能给人以启发,故有必要让其“重见天日”以便“焕发容光”。
上古即周代之前,原始社会至周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距离今天太过久远,许多历史事实早已暗而不彰。虽然许多神话、传说、历史记载等都涉及上古时期的社会生活,但真实的历史(尤其是涉及女性的)仿佛戴着轻盈而神秘的面纱,直待细心的学者抽丝剥茧般地揭开其真容。而郑慧生教授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至于为何要聚焦于上古的妇女与婚姻,作者说得非常清楚:“妇女与婚姻这个问题将贯彻人类历史的始终,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永恒的主题。”“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有妇女,社会要发展就得有婚姻。”这确实是历史研究的问题之一。
全书围绕着这两大主题,涉及了人类婚姻的起源、几大婚制的产生与发展、上古著名女性、上古圣王性别辩证、三代婚制及妇女地位等重要问题。作者以丰富的原始材料、独特的性别视角、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挑战了传统史学中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叙事,凸显了上古时期妇女的重要地位。这为我们理解上古华夏社会的性别关系与权力结构提供了一些颠覆性的解读框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的起源。
三大维度重塑上古性别叙事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充满了各种大胆的“奇思妙想”,但作者并非信口开河,而是秉持着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念,通过对神话传说、传世文献、考古遗存、石像图像与古文字材料的细致分析与解读,得出了一些乍看之下“瞠目结舌”的结论。虽然其结论未必受到普遍认可,但其论证却仍值得后来者学习。
该书系统梳理了从原始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演变。婚姻制度的演进在书中被划分为多个清晰的阶段,最终在父权制下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但此一夫一妻制的实质是男性可以多妻而女性只能一夫,这与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一夫一妻制迥然不同。在作者看来,婚姻制度的演进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直线式进步,在某一时段或地区完全有可能存在迂回与曲折。
该书提出了女性是上古社会领袖的诸多论断。作者系统论证了黄帝、炎帝、尧等上古帝王的女性身份。他引述闻一多对神话传说的分析,指认后世试图把女娲、羲和颠倒为男性,论证黄帝到尧都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女酋长,作者通过细读《山海经》《大戴礼记》等典籍,分析甲骨文“帝”字等字的文化含义,试图揭示出一个被后世文本遮蔽的真相: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很可能是母系氏族的女性首领。
这种解读太过大胆、太过新奇,不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但学界持此说者并非没有,只是相对较少。不过,其在分析上古史时对女性视角的运用,确有可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如对“鲧腹生禹”传说的重新诠释,就令人耳目一新。传统解释往往陷入男性生育的悖论,而作者指出这是母系社会记忆的残留,鲧其实是禹的母亲。这一发现不仅解决了《天问》“伯鲧腹禹”的千古疑难,更揭示了从“公天下”(母系分配制)到“家天下”(父系宗法制)的权力转移过程。即便其在分析某些具体问题上推论太过,但作为一种思路,在分析其他问题上也有可能会取得奇效。
依作者之见,母系氏族时期,女性作为氏族核心享有崇高权威:西王母之人兽相杂的形象实为母系氏族酋长的图腾化写照;羲和创制历法反映了女性在天文领域的贡献;女娲补天可能是母系首领组织抗灾的历史记忆。可自从夏代确立父权制开始,妇女地位直线下降,商代虽然仍保留着母系残余(如妇好领兵作战),但男性已掌控了核心权力;到了周代,“牝鸡无晨”的训诫彻底剥夺了妇女参政的权利,“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的礼制更将女性禁锢于家庭领域。妇女地位的沉降更表现在婚姻制度上的嫡妾之分:西周“诸侯一娶九女”的滕妾制,使妇女沦为生育工具,“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的记载,更暴露其物化女性的倾向。
在这种视角下,一些习以为常的故事往往被解读出新意。如常羲(嫦娥)“奔月”被解读为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这个案例打破了“妇女完全被动”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历史主体性的复杂面向,从侧面反映出在母权滑落与制度变迁中势必会出现一些反抗者的现象。
学术意义与现实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30年前的著作,甚至具有一定的范式革命意义。郑慧生打破了传统史学“男性创造文明”的叙事框架,证明女性不仅是上古历史的参与者,更是制度创造与文化编码的主体。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认识论革新,比琼·斯科特《社会性别:历史分析的一个有效范畴》的宣言性论述更早地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范本。
当然,作为一部著作,甚至是一部“旧作”,其自然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该书也存在一些局限,有些推论稍显大胆,论证的支撑材料有限,证据不足;该书深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对婚姻制度的功能主义分析略显单一;对周代妇女地位的论述偏重上层,缺乏平民女性的史料支撑等。但瑕不掩瑜,其核心论点都具有一定的证据链,如以商代“无嫡妾制”与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对比,清晰地呈现了制度转型的关键节点。
总之,该书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命题:华夏文明的源头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性别权力结构。当炎黄二帝等“人文初祖”被还原为女性身份,当婚姻制度的演进与权力更迭的关联被揭示,这就不仅仅是对历史细节的修正,更涉及对整个文明叙事框架的重构。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但其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忽视妇女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不要忽视那些被正统叙事遮蔽的声音!文明的真相可能就藏在神话与史实、文字与器物的轻盈面纱之后。
揭开上古社会神秘的面纱,既是该书作者所做的工作,也应该成为有志于上古史和妇女史研究的后辈学人努力的目标。在该书的结束语处,郑慧生教授说:“衷心希望一部一部的妇女史著作不断出来。”这是郑慧生教授当年的心愿,如今正在一步步变成事实。
该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上古妇女与婚姻的专著,其恒久的价值正在于此。在女性主义史学勃兴的今天,我们更要正视历史中性别的不平等起源与差异化叙事,如此,才有可能更确切地理解当代女性解放的深层意义。而这些都需要更为坚实的当代妇女研究成果,只有奠基于此,当代妇女研究才能更上层楼!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