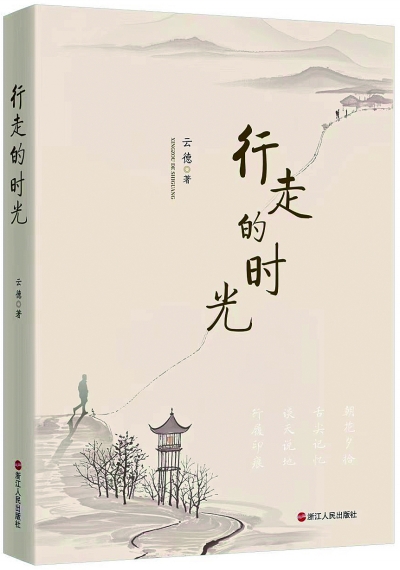
■ 云德
早在退出工作岗位之前就已下定决心,为自己规划了退休后的唯一任务就是彻底退出江湖、回归家庭,读闲书、慢生活、会友朋、看世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两三年坚持下来,优哉游哉、轻松愉快,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总忍不住涌出一种“没事偷着乐”的惬意感觉。
忽一日,与业界几个老朋友小聚,席间大家纷纷诉说着因“被安排”而忙碌不堪的辛苦,唯自己笑而不语。没想到的是,有位曾颇负盛名的文坛大佬聚会散伙后,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老弟的做法我不反对,处在一个热衷功利的社会环境,退下来能甘于寂寞,不参与他人事务、不为名利奔忙,也是难得的享受。但是远离喧嚣,并不代表无所事事、荒废自己。即使原有专业可以放弃,闲下来写点感想和随笔之类,给自己留个念想,也算是无负过往了。”
老兄一番话,振聋发聩,顿时令我沉思良久。悄然暗想,到了这把年纪,既不用为稻粱谋,也没有名利之惑,更不存在担忧他人毁誉的虚荣心,即便是纯粹为了防止大脑萎缩、小脑退化之类的生存之需,在闲云野鹤、青灯黄卷之外换个活法,亦未尝不可一试。
于是很快静下心来,列出一串题目,走进了从未涉足过的随笔领域。未曾想动起笔来倒也比较顺手,一口气写出七八篇小文。试着投给相关报刊,竟然颇受编辑青睐,最初的几个月,北京的几家报纸几乎每周都能看到这些小文章。朋友和同事们在普遍惊讶于过去“板着脸孔”搞评论的人,竟然和颜悦色地改行写这等闲适文字的同时,既给以善意的小挖苦,也给予热情的表扬与鼓励。特别是那位当初也曾竭力劝我动手写点东西,甚至不断出命题作文的作家老友陈建功,反倒不时拿我开涮,常在朋友聚会时满脸坏笑地调侃说:这哥儿们看来,要拉开架式抢我们的饭碗!
抢人家饭碗的事情咱干不来,况且也没那本事。文学创作需要才分,自我揣摩没那两把刷子,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写惯了公文和理论文章的人,事先需要大量的案头准备和观念预设,措辞推敲时谨小慎微的过程往往会耗尽所有的烂漫激情,而属于风花雪月类的随笔则完全没有固定的格式与模板,可以信马由缰、海阔天空,更兼成败皆可坦然的尝试以及自我找乐的闲情逸致,让自己心态特别放松,写起来没有丝毫顾忌与压力,正如常年负重爬坡的人突然间卸下包袱,两手空空、闲庭信步,全身心解放的轻快感瞬间也就变成了难得的精神享受。故而,这批随笔虽题材驳杂、主旨多元、形式不一、难合成规,却也多少有了几分机杼旁出意外之喜。新手的好奇和欲罢不能的惯性,竟把一个文坛老炮莫名其妙地蜕变成一枚散文新秀。
写了半辈子评论,除了友朋和熟人外,基本上都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而改写随笔后,这些千字小文一经见报即颇受待见,总有众多大小网站链接,读者和网友还不时附上热情的点赞与跟帖。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一个随笔初学者的莫大鼓励。同时也不由感慨,散文随笔确乎要比文艺评论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东文学”。近两三年,他们一直把“云德随笔”作为公众号的一个品牌栏目,这本小册子中收录的所有作品,不仅全部都在公众号上集中推出过,而且每次推出时都还精心配有一段“编者的话”,无论是内容提示,还是作品评点,都不吝热情赞许的话语。
诸如:“云德随笔近来突现于京城各大报纸副刊,四处开花,闻名遐迩。”“如春天一般,带来了风,带来了雨,带来了绿叶细枝,带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带来了民众的喜欢,独独不讲台面上的套话。”“紧贴地面生长的,一是草木,二是云德随笔,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作者以它独有的行文方式,于普通生活中锤炼出美文迷人的光芒。”“叙述语言,看似朴素,却显老辣,尽藏玄机,不是一般功夫作者所能及;作品的构思,基本呈金字塔形,仿佛于浩大的沙漠中间,聚沙成基,基上加垒,最后,是主题的光芒闪烁,照亮整篇。”
——“‘你应该为生存而食,不应为食而生存’,这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的。而云德随笔生动地演绎了这个生活中的哲学。不管是一块月饼,还是甏肉干饭,抑或一碗家乡的糊粥,他都把触角伸向这个领域:《中秋月饼》中的父爱形象,《甏肉干饭》中作者的痴迷,《家乡的糊粥》中的祖母,他们身上体现的坚韧的生存意识,令人心动。”
公众号的集中推出,让原发报刊的影响获得了更大的外溢效应,朋友、同学和同事纷纷为我的改行点赞,不断以短信、微信和电话的方式给予热情地褒奖和鼓励。几年下来,劝我结集出版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出于一个新手的不自信,这事总让人心怀忐忑、一拖再拖。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此事特地请教了资深的出版专家邬书林老兄,不想这位老同事竟然给予了十分积极的回应与认可,并督促我尽快动手编辑完成。无意中倒让这位老同事为这本小册子充当了一回催生婆的角色。
书中随笔所涉及的内容,有过往岁月的回望、有人间美味的反刍、有触景生情的议论、有生命旅程的追记,之所以取名为《行走的时光》,意在追溯光阴流转的片段记忆,表达一种“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亦安然”的特殊心境,虽世事沧桑,唯初心依旧,人生漫漫、一路走来,若是无负于人、无愧于心,岂不亦可生而无憾乎?至于做到多少、做得咋样、他人能否苟同,那就只有恭候方家去评判了。
【此文系《行走的时光》(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之序言,本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