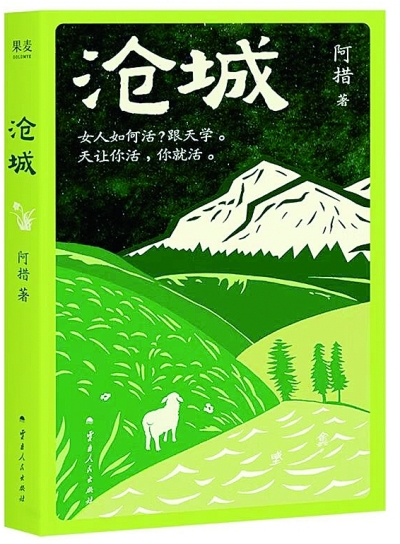
横断山的褶皱终将被阳光照亮,《沧城》为所有在暗处行走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参照:自由始于破枷的勇气,成于自我书写的坚持。
■ 李冠良
在滇西北的高山深谷间,一座名为“沧城”的小城正悄然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的新地标。青年作家阿措的首部长篇小说《沧城》于今年3月出版后,上市3个月内加印6次,纸质书销量突破4万册,电子书微信读书和豆瓣读书平台分别获得9.2和8.6的高分,被读者誉为“云南版《阿勒泰的角落》”。这部扎根边地的女性叙事,以滇西北粮仓与茶马古道重镇为舞台,通过“女伢子”“女赶马”“斋姑娘”等鲜活的女性群像,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重构了女性的主体性,让边地女性在生存实践中自然生长出的女性力量,成为当代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声音。
《沧城》的文学魅力首先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美学。阿措将故事置于滇西北的高山深谷,让雪山、溪流、茶马古道与乡野民俗成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女赶马”一生追随着马帮铃铛,在风霜雨雪中走出自己的路;“斋姑娘”虽身居庵堂,却以沉默守护着女性的尊严与知识火种。这种宗教清规与世俗生命力之间的张力,为女性叙事开辟出一个区别于都市女性文学的独特空间。作者巧妙运用甲马画等非遗技艺作为深层象征——比如水仙被掳后,臂上刺的山匪标记与她后来所见的甲马画“镇煞”图案形成隐秘呼应,地域文化由此超越背景功能,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投射。
在叙事结构上,《沧城》采用多线交织的复调手法,将水仙、阿秀、玉梅三位女性的命运编织成细密的网。水仙在暗无天日的寨子里“数着木缝漏下的星光艰难度日”,最终蜕变为掌控生死的神婆;阿秀在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撕扯中,用砍柴刀劈开命运的枷锁;玉梅则在“拍都市霓虹的间隙想起故乡的晨雾”。作者刻意让三者在章节交替中形成时空对照:前一章水仙数星的隐忍,与后一章玉梅拍霓虹下的迷茫相互呼应,既凸显女性命运的代际差异,又在节奏变换中揭示不同时代女性的共通困境。这种结构设计,让边地故事更易引发跨地域读者的共情。
《沧城》的社会价值在于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书中女性面临三重枷锁:一是儒家文化与边地民俗交织的规训,“女娃子认字是祸根”的乡谚,总在女孩摸书本时被长辈念叨;二是父权制下的暴力压迫,水仙被山匪掳走、阿秀遭丈夫毒打等情节,撕开了“贤妻良母”光环下的血色真相;三是现代化带来的身份焦虑,玉梅等年轻女性在都市与故乡的文化撕裂中徘徊。
但阿措并未止步于揭露苦难,而是写出觉醒的韧性。水仙将神婆身份化为掌控命运的武器,“女赶马”用“马帮规矩里,能走完全程的都是汉子——不分男女”回击宗族偏见;尤其动人的是“斋姑娘”,她既恪守“终身不嫁”的清规,又在深夜教玉梅识字,在经卷空白处写下:“女子的心,该比经文更宽。”这种在纳西族“不落夫家”旧俗与儒家伦理夹缝中生长的智慧,让反抗不再空泛,而是扎根于具体的文化土壤。正如书中所言:“她们不需要谁的书写,她们自己便是自己的碑。”这种觉醒从不是空洞的“独立”口号,而是水仙对生死的决断、阿秀对选择的捍卫,恰是作品对女性议题最鲜活的回应。
在女性文学脉络中,《沧城》承前启后。它延续了铁凝《永远有多远》对普通女性生存境遇的细腻刻画,但边地女性与自然、民俗的深度绑定,赋予生存图景以“野性”;它也汲取了徐小斌《双鱼星座》的奇幻寓言气质,却以“野生作者”的姿态突破学院派框架,用边地实践重构女性叙事的话语体系。
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相比,《沧城》的突破在于“女性共同体”的书写。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女性更多是自然的追随者,而《沧城》的女性则在与自然的博弈中结盟:水仙与阿秀在雪夜里分食冻麦饼,用体温焐热希望;“斋姑娘”往玉梅银饰里塞防潮草药,藏起老辈的守护。这种“野性互助”并非没有摩擦——阿秀曾骂“女赶马”“疯癫”,恰见传统观念对女性联结的撕裂。而最终的和解更显珍贵,相较《82年生的金智英》中都市女性的被动抱团,《沧城》提供了一种更具主动性的叙事范式。
《沧城》的情感冲击多层次而具体。水仙“数木缝星光”之所以动人,不仅因被囚禁的窒息感,更因那“星光”既是横断山脉的馈赠,也是女性对自由的隐秘向往——像她们祖祖辈辈仰望的雪山,遥不可及却始终是方向。而当水仙成为神婆后说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时,那种破茧的力量,让每个挣扎过的女性都能照见自己。
母职书写尤具穿透力。玉梅的母亲总说“女人的根在灶台,不在外面”,为供儿子读书悄悄卖掉银镯子,这种“自我献祭”在滇西北宗族结构中被罩上“家族荣耀”的光环。而玉梅回乡开民宿、带动乡邻时,与母亲的对话“灶台能热饭,可女人的心得热整个日子”,既揭开了传统母职的沉重,又给出了平衡家庭与自我的可能。这种代际理解,最易引发共鸣。
《沧城》用边地女性的生存史诗,写出了女性议题的普遍性:无论身处边地还是都市,女性始终在为挣脱枷锁、寻找自我而跋涉。阿措用“野生感”的笔触,让那些被主流文学史遮蔽的“她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它以边地叙事的独特性占据重要位置,为所有寻找自我的女性提供了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参照:
自由始于破枷的勇气,成于自我书写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