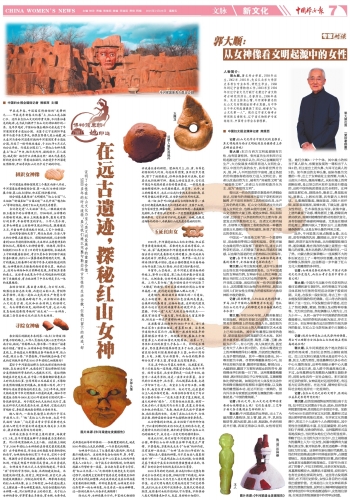郭大顺近照(受访者供图)

陶“塔”形神器

玉人
人物简介:
郭大顺,著名考古学家,1938年出生,1962年、1965年,先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研究生毕业。1968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1983年至1994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98年退休。先后主持东山嘴、牛河梁等著名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提供了实证,被誉为“红山文化第一人”。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熊维西
记者:红山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直根系,其文明起源与西方文明起源在关键要素上存在哪些差异呢?
郭大顺:东方与西方文明起源既有共性,也有显著差异。张光直先生对东西方文明起源进行比较后认为,西方以金属铜用于生产,大力发展技术和贸易进入文明社会,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将世界分为天、地、神、人不同层次的宇宙观,通过各层次的沟通取得政治权力进入文明社会。前者以改造自然为主,被称为“突破性文明”或“破裂性文明”,后者以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是为“连续性文明”。
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是商代青铜业发达,但制作的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和死后随葬,并不是用来制作工具特别是农具,生产工具仍然是石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先后进入文明社会,也都未使用金属工具。但红山文化制作大量玉器,建造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已形成了以祭祖和祭天为主要内容、高度发达的宗教祭祀文化。良渚文化拥有城市、水坝等大型建筑工程和装饰统一神徽的成组玉礼器和巨型祭祀建筑,体现了更为发达的祭祀礼仪。
中国这一“连续性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血缘纽带得以保持和延续。祭祀在强化血缘纽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共同的祭祀活动,人们增强了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期保存。
记者:在中华文明基于血缘纽带起源发展的逻辑中,女性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郭大顺:从考古发现来看,或许可以推测出女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为例,女神庙中出土的女神像,反映出当时红山文化对女性的崇拜。这种崇拜并非孤立现象,类似的还有一些孕妇塑像的出土,这些塑像突出女性的生育特征,展现出当时人们对女性生育能力的重视和对大地母神和丰收的敬仰。
记者:提到雕塑,人们往往先想到希腊、罗马,似乎中国的人物雕塑并不发达。您认为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雕塑是否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
郭大顺:早在5000年前,人物形象便已初现端倪。例如在仰韶文化时期,甘肃地区常见在器物盖上的纽处塑造人头,造型较为原始。红山文化出土的人物雕塑在艺术水准上已相当成熟。其中女性雕塑以独特的造型,更是展现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准。其材质丰富多样,涵盖泥塑、陶塑、石雕、玉雕;体积大小不一,有小巧的、有人体原大的,甚至还有大于人体2到3倍的。在东山嘴遗址出土的两尊陶塑孕妇小雕像,为泥质红陶质地,头及手臂均残缺。其中一尊体态修长,另一尊则更为丰满。尽管两尊雕像体型小巧,但特征却极为显著,腹部明显隆起,臀部凸出,大腿肥硕,腹部下方都有表现女阴的符号,使得裸体孕妇形象一目了然。这两尊雕像精雕细刻,既对特定部位予以夸张呈现,又兼顾整体比例的协调。如果没有对人体及有关动作的细微而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以及熟练的雕塑基本功,是达不到这一效果的。国内外许多专家看到这两尊女裸像的第一眼印象就是:“中国的维纳斯。”
记者:除此之外,红山文化还有哪些重要的女性雕塑出土呢?它们在造型、工艺等方面又各自展现出怎样的特点?
郭大顺: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出土了大量泥塑人像残块,如上臂、腿、肩、手、乳房及眼球等,都为泥塑,黄土质,粗泥胎,外表有细泥并打磨,表面还常涂以朱彩,女性特征明显。她们分属6~7个个体。其中最小的相当于真人原大,东侧室发现的一尊相当于人体2倍,而主室出土的大鼻、大耳可达真人的3倍。如今展出的女神头像,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出土于女神庙址主室西侧,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属高浮雕式,从贴在墙上的背部断面看,是以竖立的木柱作支架进行塑造的,这和中国传统泥塑技法完全相同。女神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耳较小而纤细,面部表面圆润,面颊丰满,下颌尖圆,富有女性特征。艺术表现技法写实,表情丰富。上唇外龇富于动感,嘴角圆而上翘,唇缘肌肉掀动欲语,面颊则随嘴部的掀动而起伏变化,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神秘感。尤其是在眼球的处理上,眼眶内嵌入了圆形玉片,让她的眼睛炯炯有光,这是女神头像的神来之笔。
此外,牛河梁第五地点陶塑女像,无头部,却有明确的乳房,腹部鼓出,双手交叉于胸前,背部平直而有曲线,从而使腰部收缩自然,通身裸露,唯在残存的左脚上竟塑出一短靿儿的皮靴,其东北渔猎人的形象特征,一目了然。内蒙古敖汉旗草帽山一座规模不大的积石冢还出土了一尊用砂岩圆雕、高度写实的神像头部残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红山文化人物雕塑的多样性。
记者:女神庙是祭祀的场所,中国古代祭祀文化历史悠久,而红山考古在其中有什么意义呢?
郭大顺: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祭祀的记载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有明确文字记载且体系较为完备的祭祀活动则始于殷商时期。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工作一直未能发现明确的祭祀偶像。红山考古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不仅发掘出庙宇遗迹,还出土了祭祀偶像、壁画、祭器以及动物神形象等。尤为突出的是,祭祀偶像以人物为主,且大小不一。从同一庙宇中不同规格的祭祀偶像能看出,当时的祭祀活动极为发达,存在主次之分。而女神形象在远古时期作为祖先崇拜的象征,在红山文化祭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记者:既然女神是红山先民祭拜的偶像,那么可以理解为女性在红山文化时期占有较高的地位吗?
郭大顺:从牛河梁遗址各个地点的积石冢的布局来看,当时社会男性占据较高地位。红山文化积石冢最大特点是设有中心大墓,其主人都为男性,其他墓葬则大多分布在中心大墓的南面,这种布局暗示着中心大墓的主人类似王者,是人群中的最高地位者。不过,女性墓葬也有规模较大随葬玉器较多的,说明女性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积石冢是对近亲的崇拜,女神庙是对远祖的祭祀,有远祖与近亲的差别。在这方面,精神信仰与实际社会地位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记者:在红山文化之后的文明中,性别地位差异是否有所变化呢?
郭大顺:总的发展趋势是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但不同文化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地位并非固定不变。如距今约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墓葬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性别地位差异。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常见三个人或两个人合葬的情况,其中男性往往随葬品丰富,且呈直躺姿势,而女性则位于两侧,呈曲身的形态。这种墓葬形式直观地反映出,当时男女地位已存在明显差异。稍晚于红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中,出土规格最大的墓葬主人为一位女性,其墓中随葬有大量陶礼器玉饰、象牙制品等,甚至还随葬一件象征权力的玉钺。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女性在特定部落或社群中同样受到崇拜,占据重要地位。再就是殷商时期的妇好墓,我们看到女性甚至也能拥有极高地位。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不仅主持祭祀,还多次率军征战,其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精美,说明商代也有社会地位崇高的女性。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在不同历史阶段,女性以各自的方式展现出重要价值。尤其是红山文化女神庙和多例女性塑像的发现,说明在以精神领域超前发展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女性地位崇高,在观念信仰发展演变中作用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