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莹,作家,广东省作协会会员。曾出版《德国婆婆中国妈》《会刻猫头鹰的男孩》《爱捡树叶的女孩》,作品曾获上海好童书、冰心儿童图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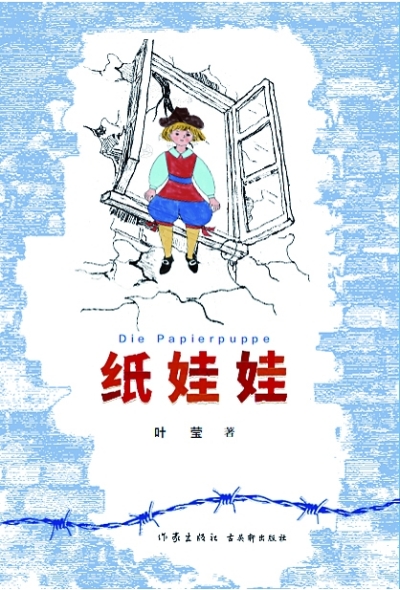
■ 口述:叶莹 旅德作家
■ 记录:田梦迪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如何把人类历史中发生过的苦难,化作孩子们能接受的生命教育?如何用儿童能理解的情感语言,讲述沉重的过往?
近日,旅居德国20多年的作家叶莹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纸娃娃》。故事始于1937年的南京:战火吞噬城池,中国小男孩田天在家园崩塌、亲人离散的恐惧里挣扎,而他的德国邻居施耐德先生和20多位国际友人一起,依托南京国际安全区,为像田天一样的20多万难民撑起临时的“避风港”。施耐德先生的外孙女乌苏,把自己最珍爱的纸娃娃送给了田天,这个小小的玩偶,从此成了田天苦难岁月里的“精神支柱”——陪他躲过大轰炸,熬过寒冷的夜,守住对家人的思念。多年后,施耐德先生的日记被发现,纸娃娃也已泛黄,年迈的田天牵着孙女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把这段关于守护与希望的故事,轻轻讲给了下一代听。
在创作时,叶莹始终抱着一个心愿:让作品跳出“苦难叙事”的局限,更聚焦“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内核。在书中,她用简洁温暖的文字裹住历史的“沉重”,让孩子知道,勇敢不只是轰轰烈烈的对抗,也可以是这样日常细碎的守护。以下是叶莹的讲述——
藏在时光里的“伏笔”
《纸娃娃》不是我“计划”出来的作品,它更像一颗被时光慢慢滋养的种子,而那些散落在我人生里的碎片,都是让它发芽的养分。
我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市的一个小山村,村口的老树下,长辈们总爱讲蔡廷锴军长的故事——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英雄,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里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的炮火。后来我在廷锴小学读书,校园里的纪念碑、墙上的英雄事迹,鼓励着我们这些后人要自强不息。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历史传承”的深意,只觉得这些故事值得被永远记住。
再后来,我远嫁德国,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德国公公就是那段战争岁月的亲历者,他18岁时本该拜师学做鞋匠,却不得已去当了兵。德国战败后,他成了战俘,先是被苏联红军俘虏,后来转到美军营地。幸运的是,他活着回了家,只是下巴上留了一道刺刀疤。
我的公公和婆婆是在战争中相爱的,战后德国分裂,公公的老家在西德,婆婆的家乡在东德,为了和爱人在一起,他留在了东德。柏林墙竖起后,归乡成了奢望。即便后来公公患上健忘症,只要聊起家乡,他眼里仍会泛起光,反复念叨:“要和平啊,老百姓只需要和平。”那一刻我懂得,无论国籍、肤色,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对和平的渴望也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2015年,我作为翻译陪同欧洲华侨发起的“单骑送铁证,万众倡和平”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环球行活动团队,参观了位于慕尼黑近郊的达豪集中营。也是通过这次纪念馆交换史料的活动,我第一次读到拉贝先生的故事——这位普通的德国商人,在1937年南京最黑暗的日子里,和20多位国际友人一同建立了安全区,庇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他的日记里除了记下日军的暴行,还有“今天给孩子分了米”“又救下一家人”等记录,成为那段历史最真实的见证。
后来,我和一位出版界的编辑聊天,他说:“拉贝日记里关于南京沦陷的苦难记忆,和德国纳粹时代的至暗时刻很相似。”这句话突然把我心里的“碎片”都拼在了一起:我要写一本给孩子读的书,把拉贝先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但不是冰冷的历史教科书,而是带着温度的“床边故事”,我想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会有人用善意守护这个世界。
为沉重的历史裹上“温柔的铠甲”
在构思《纸娃娃》的创作时,我时常对着空白文档陷入沉思。南京大屠杀承载着太过沉重的历史伤痛,如何将这段充满血泪与绝望的往事讲给孩子听,这需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要忠于历史的真相,又要避免在幼小的心灵留下恐惧或创伤。
我想起孩子小时候:女儿旅行时没带心爱的浣熊玩偶,会认真地写明信片寄给它;儿子见小狗弄伤了鼹鼠宝宝,蹲地痛哭,此后每每路过都拉着小狗绕开。在他们眼中,小动物和玩偶都有生命,它们能抚慰恐惧,传递最纯粹的爱。我可以用这些元素为沉重的历史裹上一层“温柔的铠甲”。
于是,小田天的身边有了小黑猫,会在他离家时不舍地蹭手心,会在寒夜里用身子暖他的手,甚至在危难时挺身守护;还有小老鼠,调皮偷粮,却也在日军闯入时机智掩护。这些小小的生命让孩子感受到,就算在战争里,也有不期而遇的陪伴和藏在细节里的善意。
关于以拉贝为原型的施耐德先生,他不仅与日军据理力争保护难民,还默默关怀他们的日常:圣诞节扮“圣诞老人”送礼物,为新生儿送上白鹳玩偶来祝福。我读《拉贝日记》时发现,即使在艰难时刻,拉贝先生也会用幽默安抚人心,燃起一束希望之光。
我用“纸娃娃”这个核心意象贯穿了整部书。对孩子来说,一个小玩偶,就是最安心的“避风港”。乌苏将它送给小田天,希望它能守护他,也让他学会勇敢。“纸娃娃”,就是战火中的希望。
让《纸娃娃》带着爱与和平走进孩子心里
在《纸娃娃》中,我自然融入了一些德语词汇和风俗,比如田天学说“Guten Tag(你好)”,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文化交融的乐趣,体会“友谊无国界”的温暖。书里还写到白鹳送子的德国民俗,帮助孩子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增长见识。
《纸娃娃》出版后,我计划做两件事:一是把书寄给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世界上第一座国际青少年和儿童文学图书馆,致力于通过儿童文学增进各国孩子的理解,培养和平意识;二是推动这本书的德语翻译,希望德国的小朋友也能读到这个故事,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曾有一位叫拉贝的德国爷爷,在黑暗时刻守护过一群中国人。
我希望老师和家长能借《纸娃娃》与孩子共读、讨论:“纸娃娃”象征什么?你也有珍视的物品吗?施耐德先生的善举让你想到谁?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孩子懂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纸娃娃》最想传递的是黑暗中的希望之光——是施耐德先生们用生命筑起的庇护,是南京保卫战里誓死卫国的英雄,是南京沦陷后依然顽强抗争的人民。这份光,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