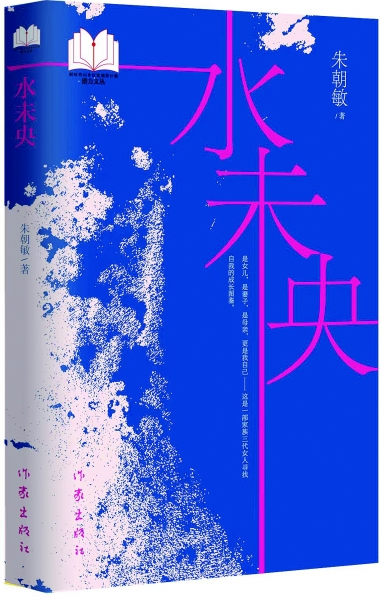

人物简介:
朱朝敏,湖北宜昌人。湖北省作协第八届主席团副主席。已出版长篇作品《水未央》《百里洲纪事》《渡与归》,中短篇小说集《渡鸦栖息时》《遁走曲》《鱼尾裙》,散文集《黑狗曾来过》《循环之水》《涉江》等。
■ 口述:朱朝敏 作家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你是否想过,一座被长江环抱的江心岛,会藏着多少关于“改变”的故事?作家朱朝敏的长篇小说《水未央》便给出了答案——通过三位女性的视角铺展“梨花岛”“后脱贫时代”的乡村建设图景,聚焦山乡人精神世界的蜕变,更有意识地构建起乡村女性的生命谱系。在个人与土地、故土与家国、历史与时代的交织中,每个生命都在生动演绎属于自己的美丽人生。
故土是创作的源头活水
我在长江之滨长大,这条江于我可非寻常河流,而是奔涌在生命里的“血液之河”。童年嬉戏、求学跋涉、成家立业,人生每一段重要旅程,都有长江的印记。
或许正是这份与长江、与乡土的羁绊,催生出《水未央》的创作灵感,让我可以在书中诉说对故土的眷恋、对长江的深情。
这份诉说的核心,是长江中下游江心那座由千年泥沙堆叠而成的百里洲。这片曾如星子般散落的“九十九洲”,终在时光里相拥成一体。我最初在文字中称它为“孤岛”,后经张莉老师建议改名“梨花岛”,添了几分清雅意蕴,也更贴近它藏在坚韧里的温柔。
“梨花岛”藏着最动人的生存悖论:它依江而生,江水是滋养万物的源头,却也岁岁受江水冲刷。三峡大坝建成前的每一个夏天,洪涝都是它必须直面的严峻考验。
这般与水共生又与水对抗的磨砺,淬出了岛上人的独特性格:既有笑对朝暮、随遇而安的潇洒,亦有直面困境、绝地逢生的孤勇。而这片土地,曾困于交通不便、以农为基的闭塞,却也意外护得一方桃源诗意;作为古楚旧地,即便时代提速的浪潮席卷而来,零星的古风楚俗仍在此间静静留存,成为乡土最珍贵的底色。
这些关于“梨花岛”的记忆,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它对我而言,从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生命的源头。即使我们为了远方远行千里,心灵却始终守着归期。
这份认知,总让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二者都是原乡的隐喻,都承载着一代人对故土的眷恋与思考。
而“梨花岛”在时代转型中的阵痛、蜕变与生态建设,更像是中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它正从依赖土地的传统农业,慢慢探索田园乡旅的新路径,不再只是提供衣食住行的物质故土,更渐渐成为能安放现代人心灵的精神原乡。这份对故土多重意义的思考,也成了我书写乡村题材的核心思路。
《水未央》中的两个核心意象,都源自“梨花岛”的真实馈赠。其一是“无忧潭”,潭底藏着与长江相通的无底洞,正因这份与大江的联结,潭水才终年丰盈碧绿、永不干涸。小说第一章便围绕这汪潭水展开,我想借它写下乡村与自然相依相生的紧密联结,就像“梨花岛”与长江,是彼此成就的共生体。
其二是梨花。百里洲本就是全国最大的梨树种植乡镇,特殊的土壤、充足的水分与漫长的无霜期,孕育出畅销国内外的砂梨品种;每当梨花盛开,整座岛屿便覆满雪白,那片纯白既是地域特色的鲜明象征,也暗含着纯净与希望的深层隐喻,是我眼中乡土最动人的模样。
“梨花岛”人或许平凡,却总能在生活的褶皱里活出力量:即便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偶发的困境,甚至荒诞的境遇,他们对生命的不懈坚持,总能提炼出明亮而纯粹的精神质地。正如加缪所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家乡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教会我这一深刻的生存哲学,也是我想在《水未央》里写给每一位读者的乡土力量。
从真实肌理中提炼人物
《水未央》中的人物,没有完全对应的原型,却都带着“梨花岛”人的影子,他们是我在驻村时观察、倾听、共情后,提炼出的乡村众生相。
我想通过他们,写出乡村人的成长与蜕变,尤其是乡村女性的觉醒。
谢翠娥是小说中的女农人代表,她的故事源于我对农村女性困境的观察。她因家庭原因患上心理疾病,却有一双做手工布鞋的巧手;在他人帮助下,她将手艺发展成产业,不仅走出了心理阴霾,还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与个人价值。
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她的“从胆怯到自信”的转变具有普遍性。农村女性中,不少人曾因家庭、身份等因素陷入自我怀疑,而自我认知的觉醒,正是她们蜕变的关键。
这种觉醒不是自发的,书中伍家姐妹与伍晓静的援助是外力,她对改变生活的迫切渴望是内力,两者结合,才让她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创业者的转变。我在她身上,集合了许多农村女性的共性:坚韧、隐忍,却也藏着改变命运的力量。
小说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伍安琪、伍枥娟、伍晓静三代女性构建的“乡村女性觉醒谱系”。这条谱系的诞生,源于我驻村时的一个发现:贫困户家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天灾人祸致贫,另一类是因家庭成员有精神或心理疾病致贫。这个发现让我心头一震,随即开始走访记录,最终统计出心理疾病患者的三种主要成因:家族遗传、特殊遭遇、家庭变故。除了不可逆的家族遗传,后两种都是后天形成的。
这让我意识到,关注乡村人的心理健康,不仅是帮助个体,更是拯救家庭、改善乡村精神面貌的关键。
我对心理疾病的关注,也有个人原因。父亲退休前一直在百里洲镇医院工作,接触的患者多是农民,他常给我讲一些“特殊病例”,其实大多与心理问题有关;我自己也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这让我在与村民交流时,能更敏锐地察觉他们的心理困境。也更坚定地将心理疗愈写入小说:乡村振兴,不能只关注物质脱贫,更要关注人的精神健康。
从构思到出版,《水未央》历时四年,字数从18万字扩展到29.6万字,几乎“改头换面”。最大的修改,是人物形象的细节化,不是增加表面的神情、对话,而是深化人物的心路历程,通过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张力推动叙事。
探索乡村振兴的精神向度
《水未央》采用“历史—当下—未来”的三重时空结构,这并非刻意设计,而是我驻村时思考的自然流露。
作为公务员,驻村对我而言既是工作,也是责任。除了走乡串户,还要参加乡村会议,针对脱贫、发展等问题研判对策。这些经历逼迫我思考:乡村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这些思考自然而然地融入小说:当下是时代转型中的乡村现实,历史是家族记忆中的乡土根脉,未来则是我对乡村振兴的热望。我将记忆、思考与祝愿融入文字,试图写出乡村的来处与去处。
在创作初期,我便确定“水”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隐喻,它在小说中承载着两层含义:一是长江文化的滋养,“梨花岛”人的生活、性格、文化,都离不开长江的孕育,家族史中的传说、习俗,也在江水的滋养中代代传承;二是乡村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从传统农业的困境,到生态建设、产业转型的探索,乡村就像江水中的小岛,既被时代浪潮推动,也在浪潮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水未央》的书名,也暗含着我的期待:乡村的发展没有终点,乡村的精神传承永不落幕。
小说中还融入了巫术招魂、石狮子传说等楚文化元素。在我看来,楚文化的精髓是“对天地的敬畏”与“物我相融的道法自然”。这些元素能在当代乡村留存,说明乡村人对故土的认知已超越了物质地域。
真正的故乡,不仅能提供衣食住行,更能提供精神支撑。而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或许就是构建这样的精神原乡,让乡村成为有文化认同、精神归宿、记忆温度的“栖居之地”。
未来,我仍会继续书写乡村,依旧以“心理现实主义”为笔,但会更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于我而言,书写乡村不是任务,而是馈赠。它让我在与土地、与人心的对话中成长,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创作,只需真诚地写出乡村的真实与温度,写出每个生命的坚韧与希望。
